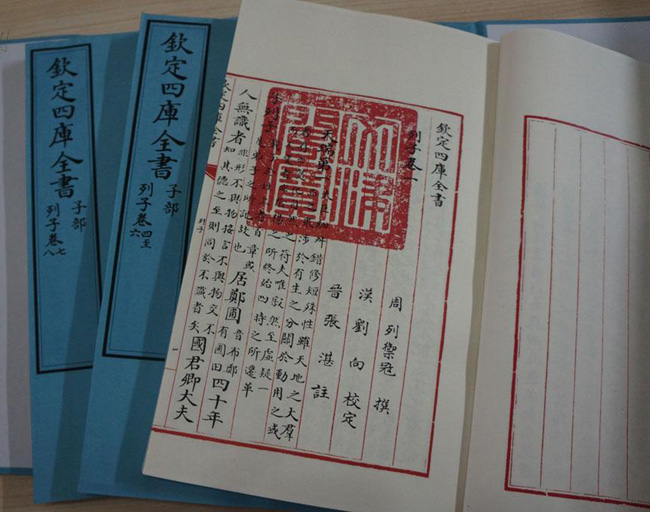
《列子·杨朱篇》蕴藏着深湛的生命哲学沉思。
孟子尝称自身所处时代“非杨即墨”,即不是归属杨朱学派,就是归属墨翟学派,孟子以两派主张“无父无君”而斥为“禽兽”,其严正之立场,标举儒家中正之教,亦无损于杨、墨两派观点之合理、可取之处也。
杨朱子之立论,颇近于老、庄、列之道家学派,主张超越世俗评价,“齐生死、贤愚、贵贱”而逍遥于物外也。
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
杨朱所言,触及了中国哲学乃至一切人类文明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万物的终极归宿都是死亡,则万物生前之善恶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此设问、推究,则必然推导出两个结论:要么,万物的终极归宿,不是死亡,死后的生命,将因生前的善恶而遭受审判(基督教)或因果报应(佛教);要么,如儒家所言:一切善恶,由于全社会对每个人行为的历史记忆、道德评价而长存,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每个人的言行、每件事的是非曲直,都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贤德之人永受尊崇,邪恶之人永受谴责!
历来论生死善恶,不出此二途:要么宗教,要么道德,宗教给予人“外在的约束”,道德给予人“内在的约束”;故而,西方文明,以宗教信仰为内在支撑;中华文明,以道德人文主义(儒家信仰)为内在支撑;伴随宗教信仰的没落,西方文明遭遇内在的衰败;伴随儒家信仰在中国被错误否定,则中华文明也处在是非不分的内在衰败之中。
让·保罗·萨特援引《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言“假如上帝不存在,则一切行为,就都是可以的了!”萨特称之为“现代历史的开端”:假如外在的约束——上帝及其宗教信仰已经遭否定,则人类行为的善恶是非,都是不分明、不清晰的,人类为什么要遵道而行德呢?萨特《存在与虚无》就是力图解决这一道德难题。他的基本思路是:假如你自我期许的事情,使你获得“自由”感(存在),那么,你就要鼓起勇气“负担”你的“自由”所带来的一切境遇,包括各种责任,因此,只要你自感“自由”,就可以拒绝那些“外在约束”(宗教以及一切世俗信念)的“假仁假义”的所谓“道德评价”,你只需“忠于自己的自由”、勇敢担当这一“自由”。
萨特的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和剧本《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都是对这一杰出思想的抒写。
儒家人文主义,不从“权利”和“自由”角度,而是从“责任”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恰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自由”不能忽视“人的境遇与责任”;儒家的“责任伦理”也不排斥“自由”与“权利”的考量。
《孔子家语》载,曾子少时耕耘,用锄不慎而伤瓜,其父曾皙一贯狂放,抄起棍子,一通乱打,曾子非但不避,还宣称:“尽情打吧,只要父亲大人能解气就行!”孔子闻而怒,告门卫:“曾参来,勿纳之!”曾参求饶,孔子教诲曰:“昔人大舜,父瞽母嚣,巧为逃避、周旋,以获两全;汝父痛打,你不跑还说好,你傻呀?!”曾子知错而改。
儒家礼教,一向以尊位慈仁、卑位忠敬为“两全之策”,换言之,礼教秩序中的双方,父子、君臣之间,是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君敬则臣忠,父慈则子孝,根本不是后来程朱理学或满清奴儒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胡扯,臣死则孤君必死;子亡则独父无养,如此胡扯,竟成为近代“批儒”之借口,荒谬至极也。
杨朱子,借管子与晏子议论养生之谈,提出了自己鲜明痛快的“纵欲主义”之人生主张: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目之所欲见者美色……鼻之所欲向者椒兰……口之所欲道者是非……体之所欲安者美厚……意之所欲为者放逸……熙熙然(放纵)以俟死……吾所谓养。
子产公孙侨,为郑国宰相,郑国因此大治。其兄公孙朝好酒,其弟公孙穆好色,子产以礼义、性命之说劝之。二人的答词,充满了人生的睿智:
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学派、道家学派,确然对个人养生、适意逍遥有真知灼见,但只可治内,不可治外也。
声色犬马,固然可娱乐残生,但礼乐仁义之道,亦不可废于人世治理也:若君臣道息、天下大乱,则个人又如何能安然纵情于声色耶?
由此可知,观点不可推之过度。
夫子曰:“过犹不及”,信哉!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