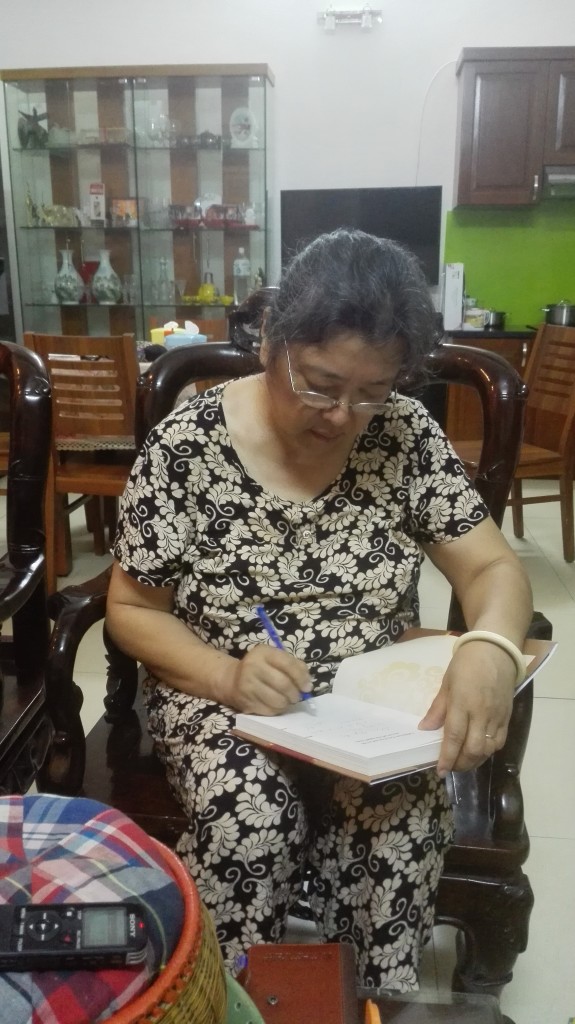7月16日至18日,中国日报常驻河内的记者有幸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访越的全程报道。其间,7月18日,在胡志明博物馆观看中越友谊图片展时,经河内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秦晓洁女士介绍,记者结识中越两国将军洪水-阮山之女阮清霞女士。7月19日下午,记者如约来到河内市阮遵路90号胡同阮清霞女士的家,倾听阮清霞女士讲述她一家三代人的中越情缘。
在阮清霞女士家的一层客厅摆放着洪水-阮山将军的雕像和画像。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记者发现,阮清霞的家,和其它河内市民的住房相似,是个四层楼房,与其它住户相连。家中内饰除了洪水将军的塑像、和油画像之外,与一般百姓的住房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记者刚走进一层客厅,阮清霞女士就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父亲雕塑、油画像等家珍的由来。记者从这位女主人的言谈之中看出这位将军的女儿对父亲的钦佩和爱慕,同时也感受到作为将军女儿的那份独有的自豪。
记者从史料中了解到,在越南现代军事史上,洪水-阮山是一位最独特的将军。除军事才能外,洪水-阮山在世只有短短的48年,却有31年奉献给中越革命,在政治、宣传、教育、文艺等领域,堪称文武双全的好手。在中国革命队伍中,像洪水-阮山这样的外国人实在罕见:3次来到中国,在万里长征中3次翻雪山过草地,3次蒙冤,3次被开除党籍,但后来又恢复了党籍。
阮清霞女士说,“我父亲最早的名字叫武元博,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河内巴亭郡安宁街。他一生中曾三次来到中国,又返回越南。”阮秋霞介绍说,“我父亲第一次到中国是1925年,他加入地下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并由阮爱国(胡志明)的交通员阮功秋送到中国广州,进入阮爱国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同年,我父亲改名李英嗣,成为李瑞(胡志明化名)李姓家族的一员,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泰国、香港。”
阮清霞说,“1929年1月我父亲再次回到中国,到中国广东东江游击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一军四十七团某连指导员。因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将红军称为‘洪水猛兽’。我父亲就跟他的一个战友说,我叫洪水,你叫猛兽,我们一起革命。后来那位叫猛兽的叔叔牺牲了。我的父亲从此就改名叫洪水。1932年,我父亲在中央苏区首都瑞金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员、马列主义研究会成员、俱乐部文化宣传部部长、工农剧社社长。1934年随同中央红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长征路上,为了不忘记越南语,我父亲每天都要阅读《金云翘传》,甚至能熟背。中国国防部的一个叔叔曾跟我说,你爸爸能用打字机写报告。我还去过我爸爸写过报告的在山西的那间民房。我父亲是同中国工农红军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的越南人。我父亲很坚强,在长征路上,他的部队被打散后,他一边放山羊,一边寻找部队,一路忍饥挨饿找到延安。我非常佩服我父亲,他对京剧很有研究,非常喜欢,他甚至还和几个越南朋友说,想在越南组织一个京剧团,让全世界都知道京剧。我父亲还担任过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副社长。1938年,为了加强抗日战争宣传工作,晋察冀边区决定出版《抗敌报》。我父亲担任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主持工作。1945年,我父亲回到越南。1946年至1950年,我父亲改名阮山。1948年1月20日,胡志明主席签署指令,授予阮山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
阮清霞女士说,“1950年底,我父亲第三次返回中国。朱德、叶剑英叫我父亲回中国。1955年9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授予洪水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据说在受军衔的时候,毛主席曾经想授予我父亲中将军衔,并就这个事情征求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志明主席说,中国是大国,还是授予少将军衔吧。虽然我父亲被中国授予少将军衔,但毛主席仍给我父亲军级待遇。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少将军衔,我父亲只能享受师团级待遇。由此,洪水成为越南中国两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两国将军。1956年9月27日离开北京返越。同年10月21日在河内逝世。”
关于洪水三次被开除党籍,又被恢复党籍,阮清霞女士说,“1934年我父亲洪水第一次被开除出党。因丢失20元‘工农银票’事件,受到右倾分子打击,被开除党籍,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洪水恢复了党籍。第二次被张国焘污蔑为国际间谍,被第二次开除出党,1936年党中央给他恢复了党籍。1938年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被阎锡山诬告,被第三次开除党籍,年底恢复党籍。”阮清霞女士说,“我父亲非常坚强,即使在困境中仍坚信自己的信念。”
图中塑像是洪水-阮山将军。墙上的照片左为阮清霞的中国妈妈陈剑戈,右为生母越南妈妈黎恒薰。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关于洪水的家庭生活。阮清霞女士说,“1924年,我爸爸(当时的名字叫武元博)16岁时,按照当地风俗与比他大4岁的黄氏艳结婚,1925年我大姐武清阁出生。在我大姐出生三个月后,我爸爸就跑到中国参加革命了。中国山西五台四区(东冶)工作期间,我爸爸与中国妈妈陈玉英相遇并迅速产生了感情,几个月后(1938年4月29日)就在东冶镇结婚了。我爸爸跟中国妈妈陈玉英说,玉英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软,还是起个硬点的名字吧,就叫陈剑戈。从此我的中国妈妈就改名陈剑戈了。我爸爸和我的中国妈妈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当时打日本,条件非常艰苦,我的这个二姐6个月时就死了。后来,1945年生了大哥陈寒枫,1946年生了二哥陈小越。我的两个哥哥目前在北京生活。”
阮清霞女士说,“我爸爸在返回越南后,得知中国妻子和两个儿子在撤离延安的路上遭遇蒋军飞机袭击丧生,经组织批准,于1947年与我的第二个越南妈妈黄氏兑结婚,生下我的三姐阮梅林,后因多种理由,两人分手。1948年10月9日,我爸爸在越南被授予将军那天,与我的生母、越南妈妈黎恒薰结婚。1950年,我爸爸被派到中国工作。到北京后,我爸爸才知道我的中国妈妈陈剑戈和我的两个哥哥陈寒枫、陈小越都还活着。我的中国妈妈陈剑戈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后,选择默默离开,牺牲自己的幸福,让我爸爸和我的越南妈妈一起生活。”阮清霞指着照片对记者说,“你看,我妈妈多漂亮。我于1949年8月15日在越南清化省出生。我小时也很漂亮,爸爸妈妈都以我为骄傲。谈起我妈妈,还是名门闺秀呢。我外婆的外公就是黄耀。在法国统治越南时期,越南皇帝让黄耀管理河内。现在的中国驻越大使馆就在黄耀街上。”
谈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阮清霞女士说,“别看我会说中国话,但我基本不认识中国字。1951年在我正在学说话的时候,我在北京生活。因为在外边朋友、老师等都是中国人,为了不让我们忘记越南语,我爸爸让我们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用越南语说话。1956年我回越南,学了一点汉语,但没学多少汉字。当时学校教俄语。后来上军校,更是很难接触汉语。之后又到部队,不用中文。1992年,我军衔到了中校之后,军队让我退休,我就退了。说实在的,我在部队工作的时候干得很好。我是学通讯设备的工程师。那个时候我管全军的通讯设备。全军有通讯设备的地方我都要去,连老挝、柬埔寨也要去。我从部队退休后,我找到胡志明主席的秘书,我说,我在军队干得很好,但军队不用我了。我跟他说,我退休后我凭我的专业可以挣钱,成为资本家都没问题。您跟胡伯伯汇报一下,我去挣钱,挣很多钱。我还跟军队的领导说,两三年后,我就买汽车,我带你们去玩。当时我就开始与中国人一起做边贸。当时越南军队用的电台很多是中国援助的,由于两国关系不好,电台坏了,没有零件配,部队的人就让我到中国去找。从那开始,我就重新开始用汉语。记得当时中国人和越南人谈一笔生意。他们之间用英语谈判,所签的合同金额有几千万美元。中方的是总经理、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越方的是将军。我用中国话和越语在他们之间沟通。他们要不只懂语言,要不只懂通讯设备方面的技术。而我不但懂语言,还懂技术,双方不懂的词汇,我用中国话和越南语来解释。等双方都搞懂了以后,就用英语签合同。他们双方最后都受到各自单位的表扬,而我呢,收到了我的翻译稿费。前一段时间,越南部队的士官找的翻译说得不准,中国朋友到我家,问我是否能做翻译。因为我小脑血栓,腿脚不利索,就让他们来家接我。等到谈判时,我就坐在边上听。5分钟之后,我就知道翻译的错误在哪里了,我马上用越南语告诉越方领导怎么去修改。最后谈判成功。就这样,通过中越之间的往来,我的中国话水平逐渐提高。当然,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也经常教我中国话。”
阮清霞说,“在中越两国交往方面,我在政治方面牵线搭桥的事情很多,这里我就不说了。在经济方面,我曾经带过350多个越南军队和民间的商务团。因为越南和中国的一些国情相似,所以在越南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想到中国寻找答案。比如,印染。中国援助越南的一种军服的颜色,越南人非常喜欢,但自己却配不出这种颜色。我就带团到中国去考察学习。我做生意一般都是正规贸易,但有时候也需要做边贸。比如中国援助越南的机器,一个零件坏了,配不上,正规贸易很难搞到,手续麻烦,又费时间,我就找人通过边贸搞到,机器就可以继续用了。从正规渠道来越南的中国货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且适合越南人的条件。”
阮清霞说,“由于家庭的缘故,我对中国人的感情很深。来越南的中国人,只要找到我,我都会帮忙。比如有的人在越南被骗了,没钱回国,我就把他送到边境。有的中国人想跟越南人结婚,而且有了孩子,但没办正规手续,找到我,我就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跟使馆人员说,他们现在有孩子了,但没办证,你们帮着在中国办手续吧。使馆的人说,大姐,您放心,马上安排人去办理。当时很多华侨要回中国,我也帮忙。”
谈到信仰,阮清霞说,“我还信佛,而且特别信。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信佛很多年了,在我家里就有佛龛。在越南有很多人信佛,共产党不限制,很多领导也常到庙里拜佛。我觉得我是受了我爸爸的遗传,敢说、敢干、敢担当。”
阮清霞告诉记者,“我现在小区做一个小图书馆。周围的人都非常高兴。这里的领导说一个月给我100000越南盾,我不要。别人,包括中国人送我很多书,我都送到图书馆让大家阅读。我每周两天上午在图书馆管理书籍。但由于我得过小脑血栓,腿脚不方便,所以下午睡觉休息。我准备出10本关于我父亲的书。目前已经出了三本。《阮山洪水将军》是我年轻的时候思念我爸爸的时候编写的,用中英越文编写出版;第二本是将军的子女和历史学家编写的《亲人口述20世纪越南将军的故事》,关于我父亲的部分,是我提供材料。还有一本是一个军队作家写的《阮山-洪水将军传奇一生》。这些书编写出版没用国家一分钱,都是个人出资。我编写出版的书,我全部送人,不出售。等我父亲去世60周年时,我还想出一本书,到时候也送给你一本。”
阮清霞女士正在给记者的赠书上签字。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当记者提出借用两本书了解洪水将军的事迹时,阮清霞女士爽快地说,“这两本书,我送给你。”在赠书签字时,阮清霞女士说,“送给中国朋友的时候,我签字就用汉字。我的名字NGUYEN THANH HA,很多人翻译成‘阮清河’,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父亲给我的名字的意思是‘霞’,这个意思不能改。”
阮清霞女士介绍洪水将军办《抗战报》时的中国战友和洪水将军的子女聚会的照片。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阮清霞女士说,“别人到中国,喜欢带回日常用品,而我带书。我回中国,我爸爸的同事、朋友会送我一些书,虽然我也看不懂,但我都带回来,然后再送人。很多人死了几年,别人就记不清了。但我父亲去世这么多年了,还有很多人记得。我爸爸的一个中国战友99岁了,他老婆也91岁了。我姐姐、哥哥、女儿经常和老先生聚会,老先生经常会提到我爸爸负责《抗战报》的事情。”
阮清霞女士和她的丈夫。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阮清霞女士还告诉记者一个故事,“我和我老公都是军人。中国曾经帮助我们打美国军队,我们是战友,这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上军校和工作的时候,我们穿的军服、鞋帽,吃的,都是中国给的。我记得,当时有一种菜,酸甜咸,非常好吃,叫‘旮旯头’,我们感觉特别好吃,忘不了那个东西。1990年有一天,我特地到中国凭祥买了几公斤的‘旮旯头’带回家。在军校老同学聚餐时,我跟同学说,今天我就拿‘旮旯头’来招待你们。大家一下子就把‘旮旯头’吃光了。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帮助我们打美国。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喜欢吃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多了,但大家仍旧怀念艰苦的时候中国人对越南人的感情。我去中国南宁的时候,中国朋友跟我说,在打美国的时候,中国人加班,半夜也要帮助我们生产电台来援助越南。有一种中国电台102,我们用了很多年,质量特别好。我们忘不了中国军队,中国朋友,中国人民。我曾经在越南军事学院学习通讯设备,毕业后也在军队工作。我这里就不说中国援助越南武器的事儿了,因为我接触最多的是通讯设备。102电台、71电台质量都很好,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我们越南军队不会忘记中国的援助。”
阮清霞说,“我到谅山,凭祥等地,当地老百姓喜欢做生意。通过两国生意往来,两个城市建设得很漂亮。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时,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也请我参加宴会。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国际歌响起时,我就哭了。全世界共产党都唱国际歌,为什么两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打仗,关系不好呢?这是不对的,不好的事情。”
阮清霞说,“越南的一些公安、领导到我家来,一见到我父亲的相片就说,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中国就不会与越南打仗。也有人跟我说,中国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你家躲着。你说,这话好听吗?我很不喜欢听到这些话。两国打仗,对我们是最不好的,对我们家也是最不好的。昨天(7月18日)那两个副总理讲得很好,但最后要看他们怎么搞,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情。一些跟我们做生意的中国老百姓跟我说,阿姨,如果中越两国打仗,我们就不来这里做生意了,我们到老挝去做生意。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我认为两国要永远友好。当然,也不能说,两国友好了,就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国家之间矛盾总会有,但可以谈判,说各自的意见。两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能见面就只是好话,要实事求是,两国都有困难,互相了解,互相帮助,把事情做好。毕竟两国现在还是由共产党领导。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昨天(7月18日)中越两国副总理在午餐会上说,‘全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多了,但中越都是’。我们两党、两国之间有什么事情要好好谈,不要做得太僵。太僵了,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父亲那么多年在中国,中国也很多年帮助我们打美国。这也是很厉害的,不容易的。谁能忘记这些呀?谁也忘记不了!我们越南谁也忘不了,特别是我们军队。”
阮清霞女士向记者展示朋友赠的字画。摄影:中国日报驻河内记者 王健
阮清霞指着一副字画,告诉记者,“你看,这幅字是越南中部师范大学的一个书记给我写的中文”,并让记者读给她听:“洪水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抗敌报初创时期负责任人之一,对敌后游击办报做出贡献,是我们的老战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令人深深怀念。”
阮清霞告诉记者,由于自己不认识汉字,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字画后问是什么意思,自己也解释不出来,所以请求记者帮忙将这段文字用简体汉字打印出来,并翻译成越南语,放在字画下面,供越南人阅读。
谈到新一代对中越友谊的传承,阮清霞女士说,“从2006年,从我父亲逝世50周年开始,我给越南河内大学中文系学生颁发阮山-洪水奖学金。开始的时候,我给两个名额,每个名额200万越南盾(相当于100美元)。我还给中文系送书。去年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姑娘(是越南军队一位老战士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工作)说,因为中国特别好,你父亲特别有名,想参加赞助。最后她同意每年持续向中文系的两个大学生赞助奖学金。今年在北京居住的大哥陈寒枫、二哥陈小越说,我们都是越南的孩子,每年给两个学中文的越南大学生捐助奖学金。到目前为止,通过我,从开始捐助两个大学生,现在可以捐助6个大学生了。”
阮清霞告诉记者,每年颁发奖学金的时候,都要做报告,告诉这些中文系的大学生三点:第一,通过汉语,可以了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的文化。第二,学汉语,就有条件阅读越南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因为越南祖先过去也使用汉字。第三,要学习洪水-阮山精神,即便在长征途中,为了不忘越南语,每天仍坚持阅读背诵《金云翘传》。
阮清霞说,“我的事业后继有人。”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何氏蔷云,1975年生,学生物专业,在科学院研究食品防毒,在日本攻读博士,她老公也在读博士,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二女儿何氏蔷秋,1976年生,也是共产党员,目前是越通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过汉语。二女儿小秋经常从中国回越南帮助我做中文系大学生助学金的事情。”
阮清霞告诉记者,何氏蔷秋在北京作采访工作,开始很多老人不愿意接受她的采访,但得知是洪水的外孙女时,都愉快地接受采访。所以,何氏蔷秋常说,由于有外公和中国外婆的保佑,在中国工作非常顺利,其它同事都愿意跟着她去中国各地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