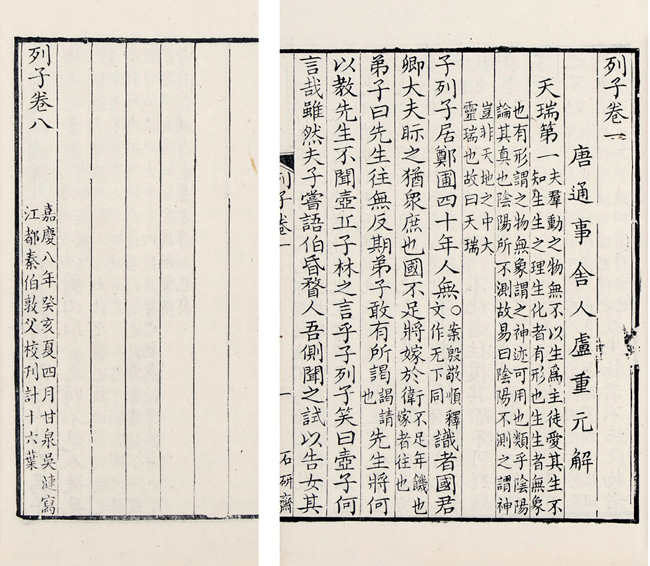
列子的老师壶丘子,曾精湛地教诲列子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视。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观矣……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世俗之人大多玩物而丧志,皆因不知“外物”之“来也无故(缘由、逻辑),去也无影(归宿、逻辑)”,波斯诗人哈菲兹、法国诗人龙萨均有诗咏之:“去年白雪,而今安在?”;与此同时,“我”亦飘忽不定、反复无常:假如天气晴和、环境安谧、“我”又睡眠充足、身心俱佳,则触目所及,皆俊男、美女,鲜美可玩;反之,触目所及,皆是粗婆、蠢汉,恶俗无比;“物之无故”与“我之无故”,皆“无缘无故”之鸟事而已矣!
驰骛于外者,谓之“外游者”,求备于外物而恒久不足,譬如妇女之于化妆品、服饰之类,其愚昧、迷乱的本性,使之“求备”而总“不备”,一生在昏乱的渴求与煎熬中度过;常见某妇女揽镜自照、顾影自怜、自怨自艾道:“咋就老了呢?”余强忍住笑曰:“一定是镜子老了,老眼昏花,不然咋会照不出万古常青的美人呢……”
壶丘子主张“游”,即“取足于自身”,而与外物嬉戏而不执著,“物游”则老,“物观”则丑,不如“游之”,即“随它去吧”,不必管这些鸟事,则自由矣、美矣、年轻矣!
壶丘子之言,颇类似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
物之外观乃假象,求备而不备;物之内视,则自足自美矣,可谓至游也!
有人名龙叔者,求医于名医家文挚说:“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彘,视吾如人……此何疾哉?”
文挚大为崇拜地说:“我经诊视,已然看到了你的心房——你的方寸之地,已经虚若太空了!你已经接近圣人之境界!你的六窍皆流通,就差一窍:把圣智当成疾病了!你非但没病,而且快修炼成圣人了!”
余举目四望今日世界,颇与《列子》所载“龙叔”同一观感:“视人如彘”,细察今日中国知识界,“如彘”者颇多,惜乎余自视不能“六窍皆通”,与“圣人之境”远隔矣。
《列子·汤问篇》记叙了许多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故事,譬如女娲炼石补天、共工怒触不周之山、鲲鹏展翅、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孔子与两小儿辨日、师文学琴于师襄、秦青韩娥善歌、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等流传千古的故事。实际上,这凸显了晚周时代中华文明传播的扩大、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更新,中华文明的足迹已经到达“终北之北”、海上众仙山、断发纹身之南方裸国等边远地带。
天下之“均”理,即文明传播之根本哲学基础——全人类的价值大一统,在《列子》中由大禹之言揭示出来:
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太岁星,乃木星,是中国古典天文星象学建构的伟大宇宙秩序之核心——日月五星及二十八星宿体系的重要一环,标记着每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和十二年的太阳年周期;由此亦可知列子生活的时代,中国天文学、宇宙学之科学思维与成就,传自大禹三王,绵亘不息,已数千年矣。
大禹之臣夏革(音及)却说:“然则亦有不待神灵而生,不待阴阳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杀戮而夭,不待将迎而寿,不待五谷而食,不待缯纩而衣,不待舟车而行,其道自然,非圣人之所通也。”
换言之,大禹之道、三王之道,是在探究、顺应宇宙星天大秩序,据此兴起一番文明事业,譬如平治水土、修筑道路、建立全国赋税制度、农耕制度、水土保养制度、九州朝贡体系、五服军事拱卫、民事协调、祖先祭祀等一系列文明制度,以保障天道井然、民生繁盛、国家稳固,人或寿或夭,皆在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体系的“人文治理”之下也。
禹臣夏革(观此命名,乃知此人为假托,与前述夏禹之言,不可同日而语也)却别有一番怀抱,主张超越三皇五帝、尧舜大禹、三王之人文治道,标举纯任自然、不思不为、不可思议、连孔孟圣人都难以通达之神秘之道。《列子》道家之言,有时过分强调了“自然无为”,忽视了“自然天道,必须与人力、人文合致”的文明妙理,这也是道家哲学,终不能主持天下正道,不能兴起文明制度与文明事业,仅为儒家学派之陪衬的深层原因所在也。
《列子·力命篇》将中国人“生死顺命”的天命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子夏之千古名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传自孔子,深入中国人的伟大灵魂,数千年而不可更易。
《力命篇》中记述的著名历史故事,譬如,管鲍之交;被孔子尊为“古之遗爱”的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将“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之刑名法家邓析,执而杀之……均饱含深湛的政治哲理和政治睿智。
其虚拟的“力”与“命”之间的对话,尤为精萃: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信命者,无寿夭;信理者,无是非;信心者,无逆顺;信性者,无安危。……独往独来。独出独入,孰能碍之?……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
孔子仁爱思想,标举天命之广大莫测,唯《易传》、《中庸》、《孟子》和《列子》最能透彻抒写此妙理。
凡俗之人,往往“贪生怕死”,却不悟“生死穷达,皆天命使然”;然天命一如天时,总有先天之时序,与后天人为之顺应两造,“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之说,则安谧驻于心,人力持之如常,毫不懈怠,则穷则安、达则稳,生则乐,死则宁也:中国人生活态度之合理安定,诚举世艳羡之一因也。
列子透彻目光,横扫士农工商之世俗社会:
量与不量,料与不料,度与不度,奚以异?唯无所量,无所不量,则全而无丧。……农趋时,商趋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农人追天时而耕作,商人趣利润而经营,工匠斗技艺而称巧,仕宦逐权势而进阶,其所居之职业分野,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然而,农耕尽力而有歉收,商人蝇营而有赔本,工匠炫技而有败笔,仕宦狗苟而有蹉跌,天命使然,又何怨?
昔者,齐景公曾游于齐国都临淄郊区之牛山,见青山壮丽、物产丰饶、齐国繁荣无比,泫然流涕道:“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滴滴去此而死乎?”
“滴滴去此而死”乃精妙形容,人在分秒点滴之间奔赴死亡之常态。古今中外,贵贱智愚,皆同然而共悲也。
左右陪侍之人,无不掩泣。
唯独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子,不哭反笑。
景公问焉:“爱卿,有何见教耶?”
晏子答:“如果贤德勇毅之君,恒常在位而不死,则吾君,此时尚在田野中,为一介农夫,正为收成犯愁呢,哪有时间忧虑死亡这种贵族风雅的哲学问题呢?正是因为不断有人立于君位,又不断有人丧失君位,吾君才能如今,立于此位呀!不思大道常理,而忧虑生死飘忽,是不仁之君;左右推波助澜,是谄谀奉承之臣,所以我暗自发笑了!”
余撰此稿,品味晏子之言,真如佳酿也!
齐景公恍然大悟,自感惭愧,举觞自罚。
那些随之掩泣的左右谀臣,亦被罚二觞。
峰按:齐景公为齐国学术重镇“稷下学宫”的主要赞助人,其人颇有好学、纳谏之美:某年轻卫士,当阶侍卫之时,爱慕景公之美貌,情不能持,景公觉,命推出斩之。晏子以“拒欲不道,恶爱不详”为由,加以劝谏,景公欣然纳谏,命释放之,且戏言:“寡人沐浴,当招之抱背”,齐举国闻之而欢然,贤其宽容大度,有风雅也。
读《列子》此条记载,不仅知天命哲学之深入中国人心;齐国君臣之睿智开明、纳谏如流;更思慕晏子独立不羁、率真潇洒之风度;晚周诸子百家之灿烂风雅,真举世罕匹;反观今日学界之鄙俗不堪,亦徒增浩叹者也。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