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是什么?连同这一问题,必须率先加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关乎人类生命的紧要知识?
自1700年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启蒙主义式的回答,正把全球文明引向灾难——2016年春夏之交,全球生态系统遭遇“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困扰,极度的炎热使高温地区大量人口热死,饱受美国无端挑起的阿富汗战争与炎热的多重困扰,阿富汗当地专门负责掩埋无主尸体的工人,趁着少许清凉,赶紧预先挖掘出能容数百无主尸体的大坑,以便热浪来袭时,能较为方便地把街头热死的尸体丢入大坑掩埋!
启蒙主义的基本预设——人类工商科技知识的增长、政治-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带来人类自我控制以及自然生态控制等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启蒙化、理性化、人道化——最近300年的历史,已一再宣告这一自我标榜的神话的破产。
以予所见,论述上述问题最透彻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历经革命动荡、曾遭苏俄政府驱逐、被迫终身流亡、迭遭20世纪欧洲及全球的各种残酷战乱(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大屠杀、大清洗、冷战等)而忠贞不屈加以写作的伟大贤哲、俄国哲学家谢苗·路德维科维奇·弗兰克(1877-1950)。
1877年1月16日,弗兰克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之家。1899年在席卷全国的学潮中,22岁的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生弗兰克,本着大学生的浪漫激情,因积极参与学潮,被仁慈的沙皇政府判处极轻的“驱逐莫斯科之外两年”处罚。他游学欧洲各地,毅然放弃了左派意识形态,成为1901-1922年俄国伟大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1912年,弗拉克大学毕业,受聘为彼得堡大学副教授,1915年发表了硕士论文《知识对象》,引起广泛关注。峰按:沙皇所办大学好厉害,本科毕业,没有硕士学位,就聘其为教授,且尚有“前科”!真乃“不拘一格选人才”也。
1922年,弗拉克与一大批哲学家、艺术家,因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被苏俄政府驱逐出境。全家幸运地登上了被千古传诵的移民流亡船“哲学船”,开始了全家终身流亡并最终客死他乡的生涯。他受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佳作叠出,还与历史哲学大师别尔嘉耶夫等人,组建了宗教哲学学院,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的学术代表作是光辉之作《生命的意义》等。1939年,他又出版了大部头代表作《不可理解之物》。二战爆发,他流亡英国。战后则出版了《上帝与我们同在》和《黑暗中的光明》等论著。1949年,他完成了总结性的伟大著作《实在与人》,转年在伦敦去世,享年73岁。
海德格尔在他著名的“哲学遗嘱”——写于1966年、指定西德《明镜》周刊在他死后十年即1976年才公开发表的著名文章《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中,预言:“西方哲学必须自救,而不能仰赖东方思想——即中国思想与俄罗斯思想,从外部加以拯救”(大意)。
就目前“全球知识界”的实际情况(至少从2000年至今)来看,当代西方的、俄罗斯的和中国的哲学思想,都仍被启蒙-自由-实用-实证主义等海德格尔所毕生厌恶、批判的“对存在的遗忘”所笼罩与捆绑,确实乏善可陈。
倒是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二战前成名的哲学大师,其成熟、完善于二战或其后的伟大哲学思想,足以重新唤起海德格尔所谓的“对存在的记忆”、“对天命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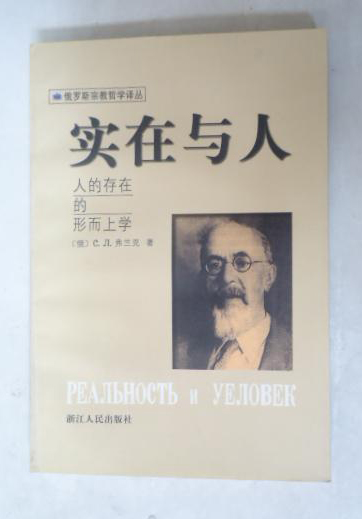
谢苗·路德维科维奇·弗兰克的《实在与人》发表于1949年,与同年发表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不朽巨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同一睿智;恰是在后者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伟大的“轴心时代”理论和历史分期,他对启蒙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对启蒙史学自欺欺人地判定“古不如今”说,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堪称反思“启蒙以来近代世界根本问题”的光辉之作、现代历史哲学的扛鼎之作。
弗兰克根本不是主流知识界、出版界予以狭窄定义与分类的“宗教哲学家”,而是具有很高的原创性、运思极其深沉的“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家”,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鼎足而三。
全球主流而庸俗的知识界、学界对他的错误归类与诠释,恰如同反复从自由主义出发、纠缠海德格尔所谓“纳粹问题”一样,反映了启蒙-科学-实证主义主流学界,对尼采、海德格尔、弗兰克等人思想的一贯偏见、歧视、打压。
弗兰克在《实在与人·前言》中自我定位道:
本书的基本构思是要克服两种信念——对神的信念和对人的信念——之间命中注定的割裂,这是近几百年来欧洲精神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现象,也是其混乱和悲剧性的主要根源。……关于经验存在的不完善,由此引起的人的个性在世界上的处境的悲剧性……应当承认,现在(二战后)盛行的关于人的生存的悲剧性的尖锐意识,包含着真理成分。
牛顿-笛卡尔虚构出“我思”(人的科学经验)的纯洁无邪、卢梭-康德伪造出的“理性”(人的社会经验)的完美无暇,被一战、二战、冷战、恐怖袭击完全摧毁了。全球混乱、生态-文明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启蒙主义伪造的神话——人的经验的完善性、合理性,人凭此杜撰出的“完善性、合理性”而废弃了“神”(自然),妄想评判一切、操控一切、改造一切,最终只能增加一切生命存在的“悲剧性”。
弗兰克所谓“近几百年欧洲精神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现象”、“其混乱和悲剧性的主要根源”、对“人的处境的悲剧性”的清醒而尖锐的意识等等,均可溯源于启蒙-自由-实用主义对“神”(超理性的万物存在、自然、道)和“人”(被超理性的自然所厚爱的个体)之间血肉依存关系(道德关系、仁爱关系)的拦腰斩断与荒谬割裂。
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等人所代表的伟大“俄罗斯存在哲学”,就是从对笛卡儿、卢梭、康德等人思想谬误的深入细致的哲学反思与批判开始的。
弗兰克对西方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笛卡尔、康德等人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性梳理,指出:在客体认识、对象认识之外,尚有一种原发性的知识类型:即生命知识。
他揭示道:“可称之为生命的知识或知识-生命。从这种精神的观点看,被我们认识的东西,不是来自于我们身外,不是某种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而是和我们的生命本身合为一体的。我们的思想,就是在显露着的实在本身的深层诞生和活动中、在它的元素本身之中实现的。被我们感受为我们的生命的东西,仿佛是自动地向我们展示自己……与这种原发性的知识相比,我们在对象性的认识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对于意识的人为压缩乃至阉割。”
对象性的认识,把对象粗暴地置放于“有用”与“无用”两大类里,再粗暴地予以取舍,从而压缩、阉割、肢解了丰富、复杂、歧义的对象本身。
依据这一“对象性的认识”进行分类、制定标准、考核、评定的现代大中小学制度体系,因其人为而粗暴地“压缩、阉割、肢解了丰富、复杂、歧义的对象(宇宙万象)本身”,必然堆积成支离破碎、百无一用、自欺欺人的知识、道德与审美碎片,而过分强调“反复考核、评定、死记硬背”的中国教育制度、学术体系,就成为全球最荒谬的制度之一。
中华民族的最深刻危机,恰恰在此。
弗兰克写道:“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知识,不是对象知识,不是作为对存在的淡漠的外在观察的结果的知识,而是产生于我们自身,在我们的生命经验的深处孕育的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在本质参与其中的知识。”
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一直到以牛顿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都是弗兰克所谓“淡漠观察外在事物”的“对象知识”和“人为压缩与阉割”,以“简化、归并、同化(实乃强暴)纷纭歧异、瞬息万变的万物现象生命”的所谓“客观物理定律”、“客观数理逻辑”,尼采所谓“同一律与因果律的荒诞”派生出来的支离破碎、局部有效、整体虚假、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知识碎片。
弗兰克进一步剖析、解释道:
不明白关于“生命的知识”这一思想的人们会诧异地问:“除了我们的知识对象的总和之外,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呢?”对此不言自明的回答是:在知识对象世界之外,至少还有投向这一对象世界的精神目光本身(孔孟谓之良知,峰按)。由这种精神目光,我们可以获得其载体或来源的神秘的、不易确定的实在性,它以不同于所有知识对象的方式显示给我们。
弗兰克扼要回顾了柏拉图、普罗提诺、奥古斯丁、休谟和笛卡尔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在缺陷、深刻问题。
他发现:“发现客体世界范围之外的实在,应当归功于笛卡尔。这表现在‘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提法中。……笛卡尔本人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发现的全部意义。他……把思维者的‘我’变为‘实体’……实际上,这里发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实在……在这种实在中,‘客体’与‘主体’是相合的。……这种实在根本不摆在我们面前充当思想所指向的客体的角色,根本不是我们在外面‘遇到’的任何东西。我们以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拥有’它,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是自己主动显现的实在,它的显现不是由于某个个别的人在看它,而是由于它的存在本身是直接的自为存在,自身透明。换言之,这种实在是以前述‘生命的知识’的形式显现于我们的。”
简言之,生命的知识,与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知识,判然有别。笛卡尔的“我思”被“我思所指向、所针对的客体对象世界”所奴役,而弗拉克的哲学天才,在于深入地思考与发现:“我思”从何而来?什么让我“思”,让我“在”,让我渴望“建立一个自明的而非混乱的世界”?“思”的本源与冲动,“思”的天赋与本能,让“我”非要把这个世界安顿得好好的(辜鸿铭所谓“永恒感与安全感”的世界)不可,在“拥有”这个碎片化观察以及勉强粘合这些碎片的对象、客体世界的背后,一个更高、更美、更广大、更充实也更自由、生机盎然的、主客统一、万物亲密无间的生命世界,一个值得“拥有”的世界——实在!
这就是孔子、孟子、子思、曾子,一直到陆九渊、王阳明等中国贤哲所谓“良知”世界、“参赞化育”的世界、“博厚高明、悠久无疆”的世界、“无声无臭、乾坤始基”的世界,即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世界——道。
万物的血肉相依、血脉相连,即仁爱这一至高无上的温情,从道中发源,沛然若决江河;我们看待万物,如同看待自己,油然而生深沉爱慕,这一过程不可究诘、不可思议,但又必须如此,中国儒家谓之“天命”。
(未完待续。)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