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论文《中国照亮世界》(在2009年11月5日“中外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研讨会上发表)指出中国儒家思想是促使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生的文明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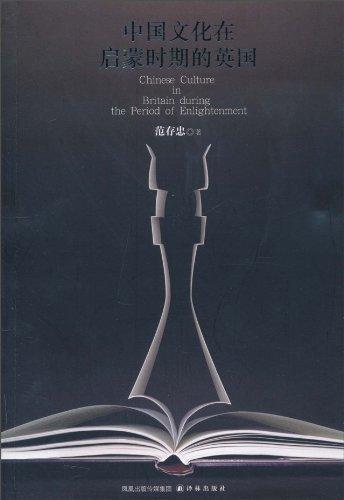
近研读翻译家范存忠先生(1903-1987)的专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11月首版,南京),再次印证了这一长期以来被忽略、遮蔽、掩盖的惊人结论:儒家人文主义思想,既是古典中国的治理核心,也是近代全球文明的启蒙者、照亮者。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用大量史料和分析,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特质,如何深刻影响了英国、法国等欧洲近代先进国家的政治、文化、艺术、风俗等诸多方面,进而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的风起云涌。
进一步阅读中西史料发现,法国哲学大师、散文大师蒙田(1533-1592)在晚年阅读了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出版于1584年的名著《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即《大中华帝国史》),遂在1588-1592年间的《论经验》中,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由衷表示钦佩。而在1590年的澳门,三位葡萄牙人用拉丁文出版了《绝妙论著》,对中国大量人口妥善分布于城乡、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科技的发达、政治宗教道德制度的考究完善等,大为欣赏。
到了1621年,英国出版了学者罗伯特·伯顿的名著《忧郁症的解剖》,书中三十多处都提到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选拔官员……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他们的老爷、高官、学生、硕士以及由于德才而升上来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贵,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
1,作为“自由思想”之源泉的孔子智慧
自马可波罗中国游记发表以来,中国被欧洲人视为传奇性的国家;到了17世纪后半叶,由于多种确实可靠的报道与研究,中国被塑造为一个富有智慧、获得成功治理的国家。
1687年,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最富于纪念意义的一年:法国教士柏应理,将利玛窦等人翻译的《四书》在巴黎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各种译本极多。
1688年6月巴黎的《学术报》登载柏尼埃的文章说:
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
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
由于耶稣会教士们对孔子学说系统、深入的翻译、介绍、研究,整个欧洲到处都能听到称颂中华文明的声音。
约翰·奥格尔比(Ogiby)在1688年翻译的《中国史新编》译者序言中,引用马加利亚内斯(Magalhanes)的话说:“中国这个国家,这样巨大,这样富饶,土地这样肥沃,气候这样温和,人口之多几至不可胜数,而他们的制造工业和治国之道又如此突出,所以我们可以老实地说……这个题目(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真是够大了……需要动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见识的作家。”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Essay 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1671)和《英雄德性论》(Of Heroic Virtue,1683)里,对孔子的德治主张,表现出高度的激赏与深入透彻的理解:“政府的管理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其间差别远不及政府管理人员的品格来得伟大。”
他概括孔子的治国之道是:“没有好的政府,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到最微贱的农夫,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思想、听取劝告、遵从法令、努力为善,发展自己的智慧与德性。”他非常推崇孔子极其杰出的天才、高超的品性,和词句典雅、巧譬善喻的文风。
在《讨论古今学术》(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ning)中,他形容中国如同一个“伟大的湖泊或蓄水池,是知识的总汇”,他比较希腊和中国说:“希腊人注重个人或家庭的幸福;至于中国人,则注重国家的康泰。”威廉·坦普尔有《文集》(1770年版)多卷问世,贤明睿智的威廉·坦普尔爵士,深深掌握了孔子治国、治人智慧的核心。
可惜僵化的欧洲天主教会,对此不加研究,就武断行事,在17世纪末屡屡挑起“中国人教派事件”:利玛窦来华,对中国固有风俗之祭祀孔子和崇拜祖先,善加容忍、疏通,且学行深湛,受中国朝野尊敬。不料,罗马教廷1704年明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引发朝野不快乃至中西冲突。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于1688年来华,归国撰成《中国现状新志》(1696)和《论中国礼仪书》(1700),备受欧洲瞩目。
李明指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西方信仰如出一源,其原始时代的信仰,完好保存在儒家学说中。孔子信天道,不信偶像,与基督教无大出入,虽然形式上属于另一系统。
中国儒生所信奉的,就是这些简单朴素的真理,与大众被和尚、道士糟蹋了的偶像崇拜不同。巴黎神学院和教会当局对此观点大为光火,竟然下令予以查禁。
孔子具有“自然神学”(deism)色彩的精辟言论,如“天何言哉”等名言,成为17、18世纪一大批自然神论者的思想解放利器。休谟在《论迷信与宗教狂热》中宣称:“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思想史家称这一瓦解天主教思想禁锢、告诉欧洲人基督教信仰以外的生活方式、信仰方式的存在,进而获得对人类历史的正确认识和人生基本问题——信仰问题的合理解决的观点,叫“来自中国人的议论”。
自然神论,兴起于启蒙早期,即17、18世纪的英法等国,这批思想家常常自称或被称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s),代表人物有安东尼·柯林斯(1676-1729)、马修·廷德尔(1657-1733)、切沃利·兰塞姆、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子爵,1678-1751)、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近代启蒙运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731年,马修·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Christianityas Old as the Creation),又名《圣经原是自然法则的翻版》,宣称:“我不认为孔子和耶稣基督教的格言有何差异,我甚至认为:前者简单朴素的语录,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比较晦涩的指示。”
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亨利·圣约翰,即博林布鲁克子爵,在1714年写给英国大文豪斯威夫特的信中说:“孔孟之道含三部分:一,个人对自己的责任;二,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三,个人对国家的责任。”
妙矣哉!我读遍近代论著,除“民国七贤”等大师外,未有如此简洁明白地说清孔子学说的伟大、简朴、深邃:人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就是孔子所谓“仁”和“义”的神髓所在。孔子告诉古今一切人类:孤独一人,无法自存、自足,唯善待别人,才能赢得别人善待;唯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了自己;这是人生、社会的铁律,也是宇宙自然的大道(即天命,我所谓“天地人大一统”者)!
博林布鲁克子爵恰切地概括、总结说:古代中国的帝王要亲自示范种田,后妃要亲自养蚕,用流汗的收获,来祭祀上帝。中国人信仰“自然的道理”(order of nature),一切后起的私人道德和公共政策,都由此推导、设立出来。
孔子的天道信仰,没有任何晦涩难明的启示,天就是自然,天道就是自然的法则、道理,因此,“生活的大原则是,理性应当统率情欲;而按照这个道理行事,就是沿着生活的康庄大道前进。”
伟哉!英国近代早期的一位军事家、外交家,其远见卓识,竟然超过两百年后的中国舆论领袖、知识领袖,不知凡几!他竟然明白:生活的康庄大道,即孔子仁爱之道!
约当1714-1718年间,伏尔泰还是20多岁的青年,就在法国与博氏订交,而在1726-1728年间,伏尔泰流亡英国,与子爵过从甚密,全面接受了其“自由思想”。
伏尔泰仔细研究中华文明,称道教、佛教是满足一般大众精神需求的“粗粮”,而孔子学说,则是中国精英阶层(儒生)的信仰与道德基础,是“细粮”、“精品”。
在《哲学辞典》“中国”条目下,伏尔泰说:“我认识一个哲学家,他的书斋里只挂孔子像,画像下有这么几行诗:
他探索思想,一点也不狂妄。且为人类,揭示那理性之光:他是作为哲人而立言,不是先知;但也怪,他的国家奉其为祖师。
伏尔泰诗歌所吟咏的,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揭示了孔子思想的实质——孔子“为人类,揭示理性之光”,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孔子在古典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孔子以哲人立言,不是宗教先知,但是,自古至今,总喜欢崇拜偶像的大众,总是把孔子打扮成宗教“祖师”,近代康有为之流,还把儒家智慧称为“孔教”,至今盛行于西方,殊为可笑复可悯:孔子是文明智慧的最高层次,无端被降格了!
2,古典中国作为全球文明治理的伟大典范
英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约翰逊、哥德斯密、罗伯特·伯顿、坦普尔等人,经过对中华古典文明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与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蒙田等哲学大师相同的结论:近代世界的政治治理与人文建设,应以古典中国为典范!
约翰逊与许多欧洲哲人一样,从利玛窦、杜赫德等传教士对中国事物的描绘中,无比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单凭人文理性和道德规范,毫不凭借各种神秘启示、宗教教条,就能公平有序地获得治理与繁荣的文明——中华文明!
苦于战乱与宗教纷争的欧洲哲人,终于看到了人类创造的最悠久文明的道德光辉,其完善的政治组织、全社会一体遵守的法令、礼仪、道德规范的法治精神、至德要道对全社会的巨大协调作用、完备的文官晋升制度、御史谏议等,彰显出中华古典民主宪政机制的巨大合理性。
这一切,鼓舞着约翰逊、哥德斯密、写出名著《忧郁症的解剖》的思想家罗伯特·伯顿、坦普尔等英国启蒙主义作家、学者们,积极借鉴“中国事物”,进而大胆探索适合欧洲文明的近代民主宪政模式。伏尔泰、魁奈等法国启蒙思想大师,更凭借对中华文明的钻研与诠释,掀起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欧洲启蒙(启明)运动。
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1733年,为其所译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洛沃《阿比西尼亚游记》精心撰写的序言中,首次提及中国人,说“他们最讲究礼貌并对各门科学十分熟练”。
他参与编撰著名的《君子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时,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一篇收入1825年的《约翰逊文集》,该文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称赞中国人说:“他们的古代文物,他们的宏伟、权威、智慧及其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无疑问值得大家注意。”
请注意,约翰逊对古典中国的“美好的政治制度”的积极肯定,这一肯定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评判的主流。
该文在赞扬了法国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 du Halde)编辑的《中国通志》(Descriptionde la Chine)具有详尽引介之功后,声称:“当他(读者)读了中国圣贤们的道德格言与智慧的训导,他一定会心平气和、感到满意。他会看到德行到处都一样,也会对胡言乱语的人更加鄙视;因为那些人断言道德不过是理想,而善恶区别完全是幻梦。”
约翰逊末句是对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讥讽,英国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哲学,有冲破天主教道德僵化的历史意义,但这派思想落入另一种偏执——忽视、否认、曲解了道德价值、文明传统、宗教信仰等事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合理性,把人类社会的根基,错误设定在实用经验、工具理性这一贫乏易变的考量之上,极容易滑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渊,这一派实用主义思想,经过美国杜威和胡适等人的推介鼓吹,误导出中国近代化的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
约翰逊从三个关键角度,抓住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层面——首先,是中国儒士阶层,对全社会的巨大楷模作用。
约翰逊精辟地指出,对中国事物的满意感觉,建立在健全的思维和细致的考虑之上:“当他熟悉中国的政府和法制以后,他能享受新鲜事物所引起的一切快感。他会对世上有这样一个国家而感到惊奇。在那里,高贵和知识是同一件事;在那里,学问大了,地位就高,升级晋升是努力为善的结果;在那里,没有人认为愚昧是地位高的标志,懒惰是出身好的特权。”仅凭知识学问,就能获得高的职位、社会地位,这在中古、近代早期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法国大文豪司汤达,愤懑于贵族统治欧洲的现状,写出了不朽巨著《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雷尔,凭一介平民的身份,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得不绞尽脑汁,妄想披上军队的战袍(红色)和教士的黑袍(黑色),更妄想通过勾引上流社会的妇女而发迹,最终被判死刑的悲剧故事。小说《红与黑》的命名、立意、主旨,就是对凭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的欧洲贵族垄断政权的控诉。
与上述深刻观察相一致,现代国学宗师钱穆,在《国史大纲》等一系列伟大巨著中,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自晚周以来,国家政权向一切社会阶层、尤其是贫寒阶层开放,其不遗余力的公平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体制,是中国远胜于西方“军功贵族”或“宗教精英”(教士)垄断国家政权的“西方专制政体”的更民主公平的政治形式,也是古典中国长期开明进步、稳定繁荣的关键所在。
其次,则是大臣与天子之间的宪政制衡关系:
约翰逊写道:“当他听到关于忠臣的记载,会更感惊讶。那些忠臣……竟然敢于指出皇上对国家法令没有遵从,或在个人行为上有所失误,以致危及自身安全或人民的幸福。他会读到,帝王们听到谏议,对大臣不冒火、不威吓、不训斥,也不以坚持错误为尊荣,而是以中国帝王们所应有的宽宏大量,心甘情愿地按照理性、法令和道德,来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是自炎黄至明朝末年,历代王朝一直奉行的华夏古典宪政体系、天子大臣之间彼此制衡关系的体现。
第三个关键角度,就是孔子学说对全中国的道德轨范作用,从天子、大臣、士子、百姓,一体奉行孔子学说,是为古典中国之“活的灵魂”,确保古典宪政合理运行的“大宪章”(辜鸿铭语)。在1742年6-9月间,《君子杂志》发表塞缪尔·约翰逊第二篇推介《中国通志》的文章,其第二部分是《孔子小传》。小传总结孔子学说为:“他的整个学说的倾向是在于宣扬道德性,并使人性恢复到它原有的完美状态。”
准此可知,古典中国“美好的政治制度”体现在,1,公平选拔士人;2,士人组成文治政府,以制衡天子贵戚的权力;3,全国上下,一体奉行孔子学说即“一视同仁地进行道德自治”的主张,确保古典中国长期开明进步、稳定繁荣的三大文明法则,被约翰逊精准地概括、表达出来了。
约翰逊在1749年发表《人类的虚荣》一诗,开篇说:“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
他向往中国的万里长城,深爱中国茶,对中国园林建筑也曾加以研究,可谓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
3,向中国古典宪政之一的谏议制度学习
十八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当政,他纠集一部分辉格党人专断独行、贿赂公行,辉格党中受排挤者与托利党结成“在野党”联盟,发起倒阁运动,中国事物(古典宪政体系)就是反专权的武器之一。
报章作家巴杰尔(Eustace Budgell)发表《致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斯书》(Letter to Cleomenes, King of Sparta,1731),宣称,高官厚禄应当归属确有功勋者这一政治准则,“此刻,最认真地遵守和执行那条完美准则的,是世界上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国,中国。”
巴杰尔宣称,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中国超乎一切国家之上。他所创办的文摘周刊《蜜蜂报》和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创办的《工匠报》以及利特尔顿勋爵创办的《常识报》等彼此声援,以中国政治与道德成就,攻击首相为首的“在朝党”任人唯亲、独断专行,主张英国政治应当学习中国皇帝、官府公开倾听臣民意见的谏议制度等古典宪政机制。
“在朝党”气急败坏,组织匿名作者撰写《一篇非正式的论文》来反击“在野党”对中国的推崇,宣称“虚伪是中国一切政策的基本准则”,但立论毫无说服力。
著名戏剧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率先把《中国通志》里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著名的后继者,有伏尔泰、阿瑟·墨菲等),掀起“孤儿热潮”,他以戏剧形式揭露首相弄权、朝政腐败等,使援引“中国事物”来批评欧洲朝政的声浪,更加高涨。
首相沃尔波尔气急败坏,唆使法院传讯《工匠报》负责人及印刷商,效果也不佳。再加上政府因错误决策在外交、军事上连连失利,沃尔波尔被迫于1742年下台。
中华古典文明的合理性、人文性、民主性,成了促使腐败专权政府瓦解、垮台的道德与舆论力量。
另一位英国大文豪奥利佛·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从1760年3月11日起,在伦敦《公共记事簿报》(Public Ledger)这一当时英国唯一的日报上,连续创作了假托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北京礼部官员及亲友之间往还信函的一组文章,名为《中国人信札》,1762年以《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出版,一举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名著。
哥德斯密是爱尔兰牧师之子,174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1754-1755年间游历欧洲,饱读伏尔泰等法国启蒙主义作品,他创作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牧师》(1766)、诗歌《旅行家》、《荒村》和喜剧《委曲求全》(1773)等,均成为欧洲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
在他发表《中国人信札》之前,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和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幼子霍勒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叔和通信》(A Letterfrom Xo Ho,1757,全称《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已享有盛名,收藏家托马斯·珀西翻译的《好逑传》与阿瑟·墨菲改编自元杂剧的《赵氏孤儿》也一时轰动欧洲,哥德斯密借此时机,以《中国人信札》来表达自己启蒙主义的人文观点。
在18世纪“中国热”中,传教士的中国观察,与商人、冒险家对中国的观察大相径庭,时常矛盾。
哥德斯密精辟地分析了两种“中国观”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在于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深度”不同。他认同于伏尔泰、约翰逊等大师的看法,认为真正有知识、有教养、有操守的中国游历家,应当是文化使者,主要任务不是描绘山川河流或勘查古庙残碑,而是要深入到受访国的人民生活之中,描绘其风俗习惯、工艺发明和学术、道德成就。
因此,曾经访问并居住在中国的传教士,接触了中国“士大夫”、研习了中国学术思想、服膺了儒家学说,故而看重中国文化的积极层面;而商人、冒险家,接触的只是沿海口岸的生意人,由于言语不通、操奇计赢,难免心存怨气,凭此浅尝辄止的片面经验,往往看重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
后者如英国旅行家邓碧安(Captain Dampier)和安逊子爵(LordAnson)的游记,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无理谩骂,不足为凭。可惜,孟德斯鸠依据这些游记,写出《论法的精神》等作品,误判“中华帝国的统治原则是恐怖”。
哥德斯密借“中国哲学家”之口说:“一个人离家远行,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和他人,那才是哲学家;要是盲目地受好奇心驱使,从一国跑到另一国,那只是个流浪者而已。”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也有类似看法:现代游客,毫无哲学气质,只是到别地、别国寻求刺激,等同乞儿。
哥德斯密笔下的中国哲学家,总结人类生活的目的,是“追求智慧,以促使生活过得愉快。”为此,应当摆脱狭隘的民族、宗教等偏见,成为“世界公民”。
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普鲁塔克、威廉·坦普尔、约翰逊等大师,都喜欢“世界公民”这一称号,哥德斯密在《中国人信札》第24函中直接将这一称号的创始人,应归于孔子名下:“孔子讲过,读书人的责任在于加强社会的联系,使百姓成为世界公民。”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作者范存忠先生,认为这句孔子的话“待考”,实际上,熟悉孔子思想和儒家文献者,当知《礼记·礼运》里的孔子名句“圣人耐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即:全人类不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而能“一视同仁”地彼此以仁义相对待。这一大同主义,乃中华古典宪政体系的固有价值,是儒家崇高弘大教化之要义。
哥德斯密在名著《世界公民》(又称《中国人信札》,1760-1762)中,对中国人治国安民的艺术(政治与道德),给予高度推崇,显示了他对中国事物的深刻洞察:
一个帝国换了多少朝代,依然如故;虽被鞑靼人征服,但仍保持古代的法典、古代的学术。因此,与其说屈服于侵略者,倒不如说它兼并了鞑靼。一个国家,幅员可抵欧洲全部,但只服从一个法典、一个君主,四千年来只经历一度长期革命。这是它特别伟大之处。因此,我觉得别的国家和它比,真是微不足道了。在这里,宗教迫害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不同主张也没有引起战争。老子的信徒、崇拜偶像的佛门弟子,继承孔子的哲学家们,只是通过各自活动来尽力表达其学说的真实而已。
哥德斯密在《中国人信札》中,以古典中国为镜鉴,深入解剖了西方近代早期文明治理的诸多流弊: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你总可以找到这样一条线索贯穿着整个欧洲历史,就是罪恶、愚蠢与祸害——政治没有计划,战争没有结果。……穷兵黩武、分散财富,难道能导致长治久安吗?……你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听到自由之声,千千万万的人为此丧命,也许没有一人懂得自由的意义。……(譬如1761年伦敦地区的竞选)场面十分热闹,虽不及中国的上元灯节,大吃大喝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候选人合适与否不取决于才能高低,而取决于款客的丰啬,取决于牛排和白兰地酒的份量。……英国的法律只惩治罪恶,中国更进一步,它还奖励善行。……(在法网紊乱的情况下,受害最深的是劳苦人民。)贫苦人的啜泣得不到注意,却受到每一专制胥吏的迫害。……(又譬如圣保罗大教堂的布道)做礼拜者不少,但乐声一停,大部分人开溜,好像原是跑来听音乐的。……再看剩下的,有的东张西望,有的向隔座女子丢眼色,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嗅着鼻烟……其中一个因为吃喝过量,另一个青年女子因为通宵打牌,都倒在垫子上睡着了。……每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去租一个会堂,都可以像开铺子那样自立门户,贩卖一个新教规。他的铺子一定生意兴隆,花最小费用就可进入天堂,那自然再好不过了。
细细研读自希腊罗马帝国以来,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核战争威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等全部西方历史,不能不承认:哥德斯密所言不虚。
作为敏锐无私的观察家,哥德斯密在肯定中国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的合理有序——开明的统治、幸福的生活、奖善惩恶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准则——的同时,也细密而深刻地指出了18世纪下半叶即满清乾隆朝政的腐败僵滞:“中国也今不如昔了:法律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金钱腐蚀;商贾们更加投机取巧,艺术科学也不如以前活跃了。”
哥德斯密对此提出的文明学解释,是中国古老的循环论哲学思想,即所谓“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政治上的一治一乱,经济上的一盛一衰,个人命运的一得一失、一荣一辱,亦即“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历史铁律。
哥德斯密援引道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超越学说,推崇每个人在小康状态下的克制平静、自求解脱。
至此,哥德斯密从启蒙主义推崇的“合理近情”的理性主义原则(Reasonableness)出发,在中华文明中,发现了高度发达的民族智慧与合理有序的文物制度,认为中国思想系统与文明制度下培育的公民,能切中当时欧洲社会文明治理的诸多流弊,启迪全人类的头脑与心智。
范存忠先生总结《世界公民》(《中国人信札》)的历史意义说:“从中国的思想文物与英国启蒙运动的关系来看,《世界公民》应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里程碑。”
今日中国,再度奋起,渴望着以“世界公民”的姿态,融入西方主导的文明潮流,哥德斯密的真知灼见、对中华固有文明的睿智剖析,均堪反复玩味、吸纳融会。
每当我在大学讲堂上宣讲孔子这一伟大智慧时,总有学生不解地问“老师要反对技术进步吗?!”我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答说:“我的主张是:富要仁义,穷要上进!既要工商科技,更要四书五经!近代大学制度、社会风俗,只讲工商科技,不讲四书五经,所以扭曲、荒芜、失败!”
伏尔泰是在近代西方,能够深刻洞悉“中国精神”与文明奥妙的诸多启蒙主义大家之一。他将《赵氏孤儿》描绘的“家族复仇”故事,全然改换了时代背景,描绘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后残暴屠杀中国军民并搜寻宋室遗孤,中国儒家士大夫臧惕夫妇毅然救孤并最终感化成吉思汗的故事。
经伏尔泰如此改写、提升,“文德”最终战胜了野蛮“暴力”,象征着文明、理性、道德力量的终极的合理性,而这种超越了工具理性亦即“实用性”层次的道德合理性,恰是“中国精神”(亦即文明大一统精神)所在!
针对这场启蒙论争,范希衡精辟地指出:
鞑靼人的代表成吉思汗征服了亚洲,征服了中国,殄灭了中国皇室,中国人的代表臧惕夫妇发扬着中国民族的道德,为保全正统的一脉,对鞑靼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抵抗。这是一场文德与暴力的决斗。最后文德的威势压倒了暴力的恐怖,成吉思汗感化了,首先向臧惕低头,战胜者接受了战败者的文化的统治。这就是伏尔泰与……《赵氏孤儿》完全不同的题材,也就是他……的命意。
《赵氏孤儿》就是影射宋元之争。伏尔泰并不知道中国作者影射的意图,却将中国作者不能明言的直接搬上了舞台,真可谓无巧不成书。然而这个巧绝不是偶然……伏尔泰对赵宋那些孤儿的悲惨结局和中国儒臣那一连串壮烈抗争是早就清楚的。他在写《中国孤儿》之前已写成《风俗论》,戈比尔的《成吉思汗及蒙古朝史》是他重要参考之一。
这部书把元人的残暴写得很详细……直至文天祥不受元职“南面叩头,从容就义”止,都写得如火如荼。这就是伏尔泰所谓之“中国精神”,也正是他在《赵氏孤儿》里所发现的“中国精神”。
伟哉“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绝不向任何野蛮粗暴的势力低头,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予以抵抗,促使其转化、提升的道德理性精神、儒家刚毅果敢的忠孝节义精神!
伏尔泰《中国孤儿》就是以“雄浑豪壮之美”(卢梭评价伏尔泰文才之语)展现了“文德”不仅有用,而且可以最终战胜“蛮力”,这不仅批驳了卢梭的“科学艺术无用有害论”之立论荒谬,也树立起“文明终胜野蛮”的全球文明史上普世进步与古今传播的伟大规律。
中国人自古信奉“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的儒家道德理性主义学说,西方近代功利-实用主义,推奉“工具理性”之“实力决定一切”说,不断侵蚀着全球各古老文明的道德信念,遂使寡廉鲜耻、急功近利之风横扫世界,并使人产生卢梭式的浪漫错觉,以为“科学艺术不足以促进人类的道德进步”,进而堕退、沉沦、偏执,反其道而鼓吹“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扬朱学派),或“小国寡民、绝圣弃智、清心寡欲”之说(老庄学派),或“严刑峻法、君尊臣卑”(法家学派)等等,均未洞悉自孔子儒家一直到伏尔泰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大道:“富而教之,富而好礼”,“齐一变而为鲁,鲁一变而为道”之博大境界与深邃义理。
每当我在课堂上宣讲儒家义理,总有学生堂下辩难道:“儒家既然很好,为何不能阻挡西方入侵呢?”我告诉他们,不能“以成败论是非”,西方近代凭借“工具理性”战胜中国,不等于中国“道德理性”有错,培根“知识就是权力”之说,可以行之一时,不能行之久远。
正确合理的文明态度是:尽量吸纳工具理性以发展工商科技,同时大力发扬中国固有之道德理性(孔子学说),以约束、规范、提升工具理性之野蛮粗暴、自私自利偏向,使之服务于人类的幸福与天下太平,而非相反。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