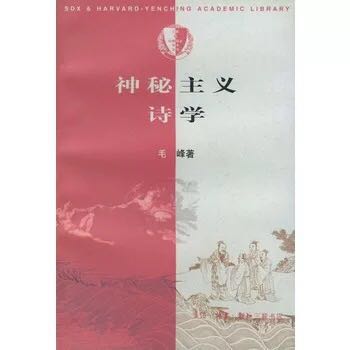
近日整理我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首部专著《神秘主义诗学》(三联书店1998,三联哈佛燕京丛书之一)时,我惊讶于自己思想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差异:在一个急功近利、寡廉鲜耻的时代,在一群胸无大志、不学无术却冒充权威、贻误民族新生的腐朽知识分子群中,我内心悲惨到极点——中国靠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终于甩掉了184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和贫弱,但中国学术思想自1644年满清军事占领中国以来僵化腐朽的质地,却毫无振作之意,根本不能与此伟大进程匹配,更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缔造出雄厚深广的精神基础。
我突然明白了18年来自己学术思想的哲学本体论——在道德精神、人文价值和学术运思、表达的风格上,与启蒙独断主义和科学实证沙文主义等西方近代主流思维势如水火,我的哲学本体论之所以标榜“诗意神秘主义”,就在于力图冲破近代启蒙独断主义对神(自然)、历史(古典文明)的大不敬与卑鄙的亵渎态度,冲破科学实证主义对学术思想固有的“诗意态度”的阉割与禁绝,将建立在“诗性体验”之上的“中国神秘主义”态度,奉为学术思想与人类知识之正宗。
在颠覆西方近代主流思维的同时,尽力吸纳、融贯西方非主流思维——反启蒙独断、反科学实证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哲学、存在哲学、新人文主义(从爱默生、惠特曼、泰戈尔到欧文·白璧德)的有益见解,使之服务于我的精神信仰——原始儒家的人文主义与民国七贤所谓“返本开新(梁漱溟)、守先待后(钱穆)”的民族复兴之路。
每当我在中国知识界陷入困境之时,我总是步入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再展阅中国典籍和西方名著,一个无需为了“黑暗、腐朽的绩效考评至上的学术制度”而粗制滥造、毫无假冒伪劣的“思想世界”,立即如清水芙蓉一般呈现,让我饱受摧残的灵魂与学术个性获得恢复与滋养,我抱定宗旨:绝不与中国当代知识界的腐朽卑琐同流合污!
人当自救,别无出路!
永远记得那个神所恩赐的清澈上午,在安静的大学二年级宿舍里,我被一本书彻底震憾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我感到周围的生活如一片废墟,以往的阅读只是翻弄一些“卖弄的词语”,而现在,一个广阔的宇宙、一个饱满的人生、一种自由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天地之间一股光明普照、生生不息的美遥遥召唤着我,使我渴望扑到大地的胸膛上,在惠特曼的草叶间,倾听闪电的起落、行星的消息。我感到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摸我的头顶,将我从泥沼中连根拔起,送我入一瞬间能洞悉过往、未来、一切存在的伟大境地……
我感到在他的诗篇与人格有一股强大的源泉,在为他提供勇气和活力,使他成为“得道之人”,能够承担任何痛苦并永享欢欣……我第一次懂得诗不是辞藻的堆砌;我第一次懂得人能和宇宙相通、能和宇宙神秘地“共感”;我第一次懂得了什麽是诗,什麽是神秘主义。那是1984年。从此,我开始对神秘主义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搜集一切有关神秘主义的资料。
大学课堂依旧被枯燥的说教充斥着。第一道思想之光亮起在一名新来的女硕士的课堂上。她叫陈淑珍。她讲的课叫《中国法律思想史》。儒、墨、道、法……各家各派的思想光辉在陈淑珍流丽的讲述中闪烁着奇彩。
我溯本穷源,借来《论语》。从此,我才懂得了中国,懂得了人性,懂得了要对天命保持信心。每当我对人世产生怀疑时,我便重读一遍《论语》,让圣人温暖的思想光辉笼罩我,使我在怀疑人性时首先让自我的“人性”获得休息和滋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每吟此句,我都双眼一热:还有比这更简洁也更深邃、更温暖也更悲凉的诗吗?我仿佛看到那个在历史的尽头、凝眸万物疾流的“思想者”苍凉的眼神,听到了他火热的心跳:努力奋斗吧!抓紧生活吧!为实现你的——天命!……
“致我爱过的所有姑娘们,现在你们已是他人的妻子,
我喜欢孤身一人,我献出这首歌,给我爱过的所有姑娘。
命运的微风不停地吹过,正是它携我离你们而去……”
这是西班牙裔美国歌者胡利奥·依格莱西亚斯所唱的名曲《致我爱过的所有姑娘们》。歌曲颤动着从古到今人类共通的一种情感:神秘的“命运感”,神奇的宇宙“微风”,它吹拂着、照管着一切存在,将一切存在带入不可抗拒的天命中,它幽深难测、玄妙无言……这是人对宇宙和生命本身——人人归属于它、它却时时将人超越和遗落——的一种既依恋又怨艾的情绪,一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诗意神秘”的情思。
正是这种“命运感”驱策着孔子以衰年之躯周游列国传布他的天命哲学和仁爱哲学;正是这种命运感,词人秦观才写下了“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何尝只是“春愁”、“闲愁”、“情愁”,它何尝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所归依的“乡愁”?
亦曾记得1989年12月深夜,我再也无法忍受在《天津日报》当一个颇为知名的记者这个被许多人目为荣耀、权力、实惠的职业的庸俗和虚假,将辞职信放在主编桌上,扬长而去。
皓月当空,夜之苍穹高远无极。我骑车归家途中,远方竟然想起了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的旋律——千军万马正在疾驰,整齐而豪迈,我震惊于古人“境由心造”哲学的真切——我也终于有望步入贝多芬所讴歌的“英雄”的行列!
我想告诉《清风庐》和《中国日报中文网·天下专栏》的读者:幸福的奥秘在于,听从于自然(神之天命)而不屈服于一个你所蔑视的“世界”(无论它是冷漠的权威或七姑八婆的训诲),你就能纵身一跃,在自然的怀抱里潜泳或翱翔了。
勇气就是生活的全部。
我周遭的一切都在堕落。
我不想与之同归于尽。
我必须自我振拔出来。
在经历了8个月的街道“待业”、“盲流”的日子,我考取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我将此比喻为新生。
在杰出的诗评家李丽中导师的细心指导下,我开始系统研究“诗学”以及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各领域。在妻子的爱、理解、鼓励和支持下,我创作出了第一批诗歌与散文。我的首批诗作、论文、三部学术专著在海峡对岸发表、出版。
在广泛深入的阅读、比较、思索的基础上,我发现了两颗闪耀不尽的思想明星: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的海德格尔。泰戈尔的诗让我想起屹立于世界最高处的喜马拉雅山的皑皑白雪。海子的诗令我落泪,他的诗风一扫艾略特以来现代意象主义诗晦涩干枯的阴霾,让我目睹了新世纪诗歌的一次辉煌的日出。
我在思考:什麽是东方智慧的精髓、源泉、新生的契机?什麽是与近代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和虚无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力量?什麽是诗的文化源泉?我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宗教哲学、易学、佛学、禅学……浏览一遍。我发现:最能说明文化的终极意义、最能打通古今中外优秀精神成果、最能整合现代物理学和现代人文思想、最“东方”、最“中国”、最“诗性”的,是中国诗意神秘主义。
我写下了超出规定字数一倍以上的、七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诗的神秘主义》,提交答辩。
当话里响起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童庆炳先生低沉温和的语调、我知道自己已被录取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奋斗赢得的命运”,也就是佛语所谓的“缘”,它神秘地推动你趋赴最适合你的生命方式和生活道路。从那一刻起,一条迷茫孤寂而又其妙无穷的道路在脚下清晰起来:作一个思想者和写作者,发出独特的言说,以生活为代价,提炼生活。
踏入北京,就踏入了一个较高层次的“名利场”。学界也不例外:有挟官自重的“官学”,有挟洋人以自重的“洋学”,有挟古人以自重的“国学”,有唯畅销是瞻的“商学”、“野学”,有靠巧立名目以自显的“后学”、“新学”……外省各路“精英”更在京都学界大展拳脚、各显神通,这些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拉拉扯扯,结帮成派……面对这种学术态势,再加上整个文化现实的庸俗化,我再度陷入精神困惑中:思之道路还如何进行得下去?
我面对古今中外的伟大诗歌文本。一股明亮的歌流从我的灵魂中慢慢升起、弥散开来、将我托举而起。我意识到这是庸人和市侩永远体验不到的“神福”、“至乐”、“天籁”。
于是我写下了迄今最满意的两首长诗《天命玄鸟》和《玫瑰祭坛-庄严弥撒》。我继续精研“神秘主义哲学诗学”:古今中外大量哲学、美学、诗学文献,每一行有关“神秘主义”的论述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脑海、我记录的笔。十几年的时间,相关资料已积累了数百万字。
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我从西学向国学转变的时期。我惊叹于现代西方哲人、诗人在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方面所做的思想贡献,没有他们那种一往无前的自由精神和生命精神,任何传统智慧的吸取,都只能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然而,人生真的如过眼云烟,只是一场本文的游戏吗?生命的真实根基和价值源泉究竟何在?我不就是为了这一探索而来求学的吗?我将目光投向东方:一个旷古绝今的伟大哲人巍然矗立眼前——熊十力!有评论称他“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这一评论尤其让我砰然心动:他的哲学一举廓清了西方近代哲学在物质-精神、现象-本体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上的重重迷雾,尤其是他“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学风,一扫当今思想界的支离破碎,在重立人生的“大本大源”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他的“体用不二”的哲学成为我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钥匙,更成为我以生命主义、人文主义解释神秘主义思想的哲学准绳。
《神秘主义诗学》从思想史中读出神秘、读出诗意、读出生命精神,它把“神秘主义”这一源远流长、波及广泛的文化现象,毅然拖离以往西方论域狭窄的“宗教学”论域(某些权威对此大为不快),使之进入“哲学诗学”的广阔视野,让东西方的诗性智慧相互激荡。
在一个生命世俗化、平面化的时代潮流前,为文化重新开启神奇瑰丽的宇宙深度之门,让人以生命精神、创造精神、人文精神驾驭物质文明,为心灵重建一个神性世界和诗意家园。
作为初步研究成果,《神秘主义诗学》中的一部分(10万字)以《文化诗学与诗性智慧》为名提交博士学位答辩,论文以全票获得通过。然而,举目四望今日知识界、出版界,令人心中顿生冷意:就当前的文化态势而言,这项学术成果即使不是“胎死腹中”,至少也得坐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冷板凳”,莫非真是“平生所学供埋骨……”(陈寅恪诗)?
我调集心中残剩的勇气,将本书草拟中的纲目寄给素不相识的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女士,自忖此番恐怕又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根本不存接获回音的奢望。当三联书店的许医农女士厚厚的回信来到我手上,我以为不过是退回的纲目或几句客气的推辞。然而,这却是一封情辞恳切、给人希望的信。
尽管我所有的单篇论文都是寄给素昧平生的杂志编辑们,他们的用稿通知书也曾令我惊喜,我的三本学术专著已经在台湾出版并广受瞩目,但这些无法与眼下握在我手中的信相比:我感到六年孤寂的学术生涯闪现出第一丝微光,它在我的学术生命乃至诗歌生命行将闭合的重要关头闪现,照亮了我的心,使我感到在日后的教书匠和写书匠的生涯之外,我仍可以写作、思考、吟唱。
我以谜一样的眼睛凝望那颗谜一样照耀我生存的“命运的星辰”。那是玉成万物的“天命”。我以百倍的奋斗去应和它。
在责编许医农老师的关怀、鼓励、帮助、支持和指导下,我将原有文字进行大幅修改扩充,形成眼下规模(40万字)的专著,基本实现了我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立下的学术写作的目标:
将生命实感灌注于学术论述,使之具有思想性、人文性、诗意性。《神秘主义诗学》成为我个人生命探索和精神探索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我把全副身心投入这一写作,日思夜想、心魂系之,既为它苦恼,又为它着迷,甚至担心:如果写完了,我该做些什么呢?生命仍在继续。写作也将持续。对我来说,思想和写作已经成为生命中必须依靠的东西。我感谢无处不在的神(自然)以壮美的词语照亮了我的灵魂与生命,让我在诗意的瞬间享受到生命的至福。感谢生养教诲我的父母、师友、亲人、神明自然。
据说,莫里斯·梅特林克弥留之际的遗言是:“永生万岁!”
所有社会-文明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命终极问题的解决。
诗性智慧以最本真的方式向人类言说他们自身,洞悉他们的生存,诉说他们的天命。诗作为文化精神,赋予生命超越乎骤存骤亡之上的“永恒”的意义、天地间“不言的”、神秘的“大美”。
中国神秘主义的诗性精神和诗性智慧揭示出文化的最深刻内涵: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就在于一种文化能将一切有声的语言、有形的文化、有限的存在向无声的语言(沉默)、无形的文化(神秘)、无限的存在(天命)转化、提升,使人类超越了狭隘的生存境界,向伟大、自由、美和创造的境界超越、飞升。
我渴望言说并捍卫永恒。
附录 《四象》
风
抚弄我们饱胀的器官
黑暗里勃起
花
开放在我们四肢中央
黑暗里交缠
雪
堆积在我们一生的每一分秒上
黑暗里明灭
月
孤独地洗出你的裸体
黑暗里,长眠。
(原载于台湾创世纪诗刊100期1994年9月)
欢迎关注毛峰微信公众号“清风庐”:houseof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