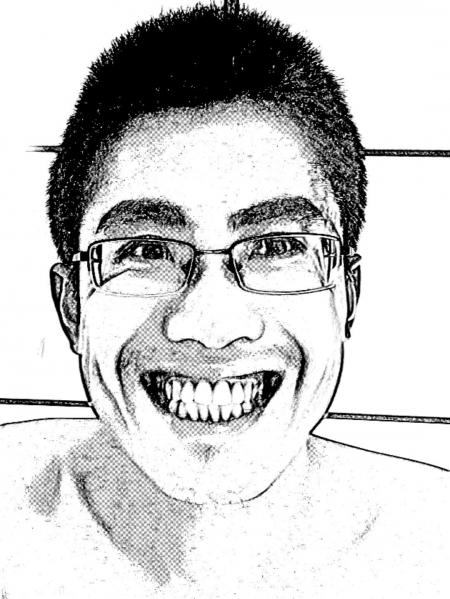从萨兰斯克坐车到下诺夫格罗得。出了火车站后,乘公交来到酒店预定网站上显示的旅馆所在地址。在一幢居民大楼前徘徊了一会,并没找到什么旅馆。幸好在两位当地老兄的帮助下,联系上了旅馆。

在他们两位的婚纱摄影室等了一会,旅馆的工作人员终于赶到了。这位老兄叫亚历克思,三十来岁模样,胖胖的,上来先抱歉让我久等。一解释,原来是我沒仔细阅读他们先前发来的邮件,找错了门。遂上了他的车。开了大约二十来分钟,穿过伏尔加河,从城东到了城西,来到一处居民区。楼房旧旧的,就像中国八九十年代的那种灰色公寓楼。他领我进了一间一楼的公寓,这里就是我要住的地方了。两室一厅,厨房浴室阳台一应俱全。对于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青旅,已经习惯了房间里人来人往的我,猛然来到这么一个“豪宅”,还真有点不适应。不过正好有机会看看俄罗斯普通家庭是什么样的,也不错。

亚历克思是房子的男主人,女主人叫奥尔加。墙上和冰箱上挂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女的照片。小儿子穿着一件红色球衣,腼腆地笑着;大儿子穿着学校制服,已经有些大人的派头。家里的陈设略显陈旧,应该住了些年头了。屋里采光不是很好,深色的家俱让整个房子显得有点暗。电视柜旁的架子上摆满了大部头的书,像是文学一类。卧室里的书架上也满满的是各种书籍,看来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书架上有一家四口的合影,一些装饰物,还有几个宗教人物画像的摆件。整个房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与一般中国的家庭差不多。
第二天在下诺夫格罗德市里转了转,看了看历史悠久的老街区,又做了游船在伏尔加河与奥卡河(伏尔加河支流)上观赏两岸风景。到了傍晚,便赶到体育场看球去了。
这场比赛是哥斯达黎加对瑞士,哥队已被淘汰,瑞士打平就可出线,原以为比赛悬念不大,况且已经看了四场世界杯比赛,新鲜感下降,觉得这场精彩程度堪忧。但一进场,就被球场热烈的氛围感染,尤其是哥队球迷,热情奔放,尽情唱着、跳着,毫无保留为主队呐喊。虽然球队出线无望,一点也沒影响他们高涨的热情。瑞士队因为只要打平就能出线,并不急于进攻,频频在后场倒球,这时全场球迷发出震耳欲聋的嘘声,对他们的不思进取表示不满。哥队秉承了拉美球队一贯的灵动球风,传控细腻却不拖踏,节奏感十足。当哥队在比赛中进球时,全场欢腾,球迷们挥舞手臂,高声唱起了“Ole-Ole-Ole”的助威口号,气氛热烈非凡,我也情不禁加入其中。比赛结束,两队二比二战平。赛后,哥队球迷依旧欢呼雀跃,喊着口号,就连在厕所里也不闲着,欢闹地唱个不停,丝毫没有球队被淘汰的沮丧。对他们来说,世界杯就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胜负固然牵动人心,但更重要的是享受整个过程。

比赛结束后,取寄存行李的小屋前排起了长长的队。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下诺夫格罗得的夜晚气温只有十几度,风吹在身上,凉意十足,困意也开始袭来。没办法,只能耐心等了。
在排队的过程中,遇到一位从圣彼得堡来的老兄。他叫麦克,也是专程来下诺看球的。麦克很开朗健谈,与我聊了很多。他比我小两岁,是那种标准的斯拉夫人面孔,深深的眼眶,淡黄头发,身板壮实。看不出,这个年轻人竟是名外科医生,平时见惯了血淋淋的场景。说起我一人来俄看球的经历,他说我勇气可嘉。回住处去的时候,因为我住的地方远,他陪我坐地铁,出地铁后又送我上了出租车,十分热情。等我到住处时,已是半夜一点了,但天空依然没完全黑下来。据说这里夏至时白昼漫长,夜晚只有三个小时。

第二天坐火车去莫斯科,又遇到迈克,打开话匣子说了许多。他说起自己因为读医学院的缘故,以学生身份得以免除兵役,我跟他讲中国因为人口多,没有强制兵役政策。我还与他分享了手机里的照片,跟他介绍我的家乡在中国的陕西省,省会是西安,我的家乡叫神木,并在地图上指给他看。他听后,嘴里重复着刚听到的这几个地名,“陕西、西安、神木”,“陕西、西安、神木”...似乎想把这几个地名刻在脑子里,认真的样子十分有趣,逗得我想笑。他又跟我介绍他们国家的好吃的,包括有名的“红菜汤”,我跟他说俄罗斯的食物“实在一般般”, 有机会在中国请他吃我们的面条,那才算真正的美食。
聊了很长时间,最后我都有点倦了,想回铺位上休息,但碍于面子,不知道如何开口。好容易找了个借口说要给家里打电话,才算脱了身。
跟麦克接触,感觉到俄罗斯的年轻人其实与我们没有两样,都渴望了解外国的文化与同龄人。在他们眼里,中国代表着一种遥远的截然不同的文化,正像俄罗斯在我们眼里一样。世界杯则提供了这么个机会,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交流,认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