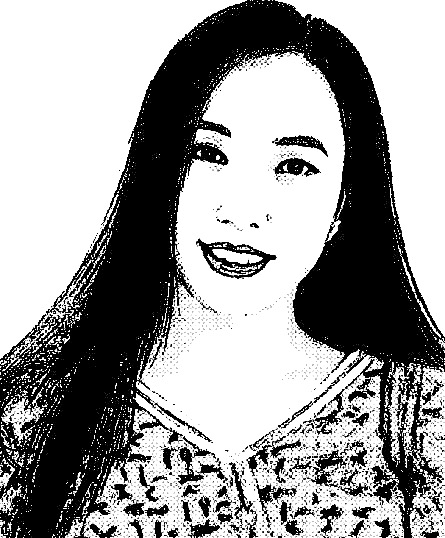德国人似乎对意大利情有独钟,所以不少德国城市都有一个意大利版的参照物,比如班贝格之于威尼斯,又如德累斯顿之于佛罗伦萨。很遗憾,我迄今仍未造访过佛罗伦萨,但是德累斯顿的确是一座令人一见倾心的城市。

这座拥有灿烂文化和艺术的欧洲古城有一种近乎忧郁的美,一座座繁复华丽的巴洛克建筑沿着易北河岸(Elbe River)铺陈开来,仿佛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建筑博物馆。虽是盛夏,但我们抵达时阳光却并不明媚,偶尔有光穿透云阵,撒在灰黑色的老建筑群上,壮丽却沉郁。
我很难想象这座在二战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的历史名城是如何涅槃重生的。 据说战后德累斯顿的古建筑废墟体积十分浩瀚,但德累斯顿人硬是将残片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收集、编号、存放,为之后的修复奠定了基础。看着那些修旧如旧、精美无比的建筑群,我除了感慨德国人的坚韧和严谨,还是会敬畏于战争的残酷:这座曾被誉为整个欧洲最美丽的巴洛克城市在1200多架英美战机的轮番轰炸下付之一炬。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曾在1945年说过:忘记如何哭泣的人,面对德累斯顿,又重新找回了泪水。时至今日,德累斯顿大轰炸依然是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

好在,时光总是能在悄无声息间弥合伤痛。如今的德累斯顿仍旧是精美的巴洛克之城,人们依然能看到圣母教堂柔美的线条,巨大的穹顶,内部精致繁复的雕刻和温暖的色调。这座代表着创伤的废墟在六十年后得以重建,而这座古城地标的重建也象征着和解、希望与信仰。只看到过去的人,除了自己的影子,什么也看不到。
当我们路过吕尔平台(Brühlsche Terrasse)的一处铁艺栏杆时,我们不约而同在一把刻有心形图案的红色锁前停下了脚步。不同于布拉格查理大桥上挂满的层层叠叠的爱情锁,眼前这一抹亮红虽然形单影只,但在灰黑色的巴洛克建筑群映衬下却更显夺目。 这让我想起影片《突袭德累斯顿》中的安娜和罗伯特,前者是战地医院的年轻护士,后者则是战机失事后被迫跳伞落到德累斯顿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身处敌对阵营的两个年轻人却因为种种际遇在战火中越走越近。古今中外,战争和爱情都是永恒的话题,而让我动容的是战争并未消弭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潜入医院寻觅栖身之所的罗伯特在上楼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德国小男孩,这个刚刚目睹了自己弟弟惨死的男孩正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前胸。罗伯特慢慢的靠近这个小男孩,故作轻松的问他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当得知小男孩想参加马戏团时,他快速说出了一位著名魔术大师的名字,并顺势给小男孩表演了几个魔术。在和罗伯特的对话中,小男孩终于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枪。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安娜看到,并深深触动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善良和良知或许并不能阻止战争,但这些人性中最朴素和温暖的力量却可以给战火伤痛中的人们最大的慰藉。
穿行于老城之中,除了感叹建筑的华美,我们还会在不经意间为民间音乐家的表演而驻足。在欧洲,街头的民间艺人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德国这样极富音乐传统的国度。但是我却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老城区见过如此众多的民间音乐家。有一阵子我曾经颇为困惑,为何是德累斯顿呢?不是海德堡也不是班贝格。后来我忽然意识到,“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在德累斯顿找到了最好的诠释。
我记得在茨温格宫(Zwinger)那位背靠着雕塑拉小提琴的中年女艺术家,英姿飒爽,还有塞帕歌剧院(Semper Opera House) 旁拉着手风琴自弹自唱的退役军人;当我们路过奥古斯特桥时,我们在桥畔看到了一个约莫十二三岁,梳着两条麻花辫,独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她的羞怯在她白皙的脸上荡漾出迷人的光彩。离她不远处有一对父女正在演奏小提琴和黑管;我还记得在宫廷教堂 (Dresden Cathedral) 旁的那对小提琴和吉他的双人组合,他们投入的神情溢于言表。 这些壮美的巴洛克建筑群为这些民间音乐家们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他们沉溺于自己的音乐之中,而周围的人群仿佛只是淡化的布景。于他们而言,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内心深处种种隐幽和情绪的表白。
德国这个音乐之乡造就了诸如巴赫、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等音乐名家,而这些眼前的民间音乐家们则让这些古老的建筑更加灵动而鲜活。时至今日,我早已记不清他们当时弹唱的曲目,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我们就这样漫无目的的沿着易北河岸走着,随着流动的音乐,直至暮色将尽。德累斯顿始终是那座黄金时代的璀璨之城。如果可以,我希望时光就此凝固,如同这周遭的巴洛克建筑一般。
原载于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