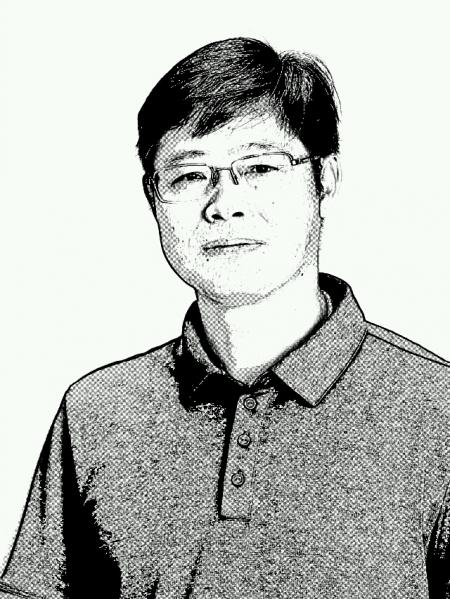人的一生,在与时间的交往中,总离不了成长的地理环境,可能要去的地方很多,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回想起已往岁月有缘去过的那些地方。在我27载军旅生涯中,到访过很多地方,时间有长有短,次数有多有少,印象有深有浅,却有五个地方在记忆深处留下了深深眷恋。第一个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世上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苏州,赋予了我生命的起点。第二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山西原平,军旅梦想起航的沐浴地。第三个地方,是九省通渠的湖北武汉,接续我人生梦想的摇篮。第四个地方,是京畿重地首都北京,成就我人生事业的高地。第五个地方,是我缘分最深的内蒙高原,深入边关哨所,走进了她的灵魂深处,在和平年代策马扬鞭驰骋沙场,走近 “战场”,在我戎马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家乡踏上北去的列车当兵,至2017年解甲回归梦里水乡,军旅生涯中遇到的、认识的便是蒙古族战友。在我军区机关工作的17年间,出差次数最多、去的地方最多,还是内蒙古大草原,平均每年一次,有时一年之中三番五次造访,时间短则三、五天,长达三、四个月,用车轮测量了八千里边防线,足迹遍布了广袤无垠的大漠戈壁,也在近距离的对话触摸中结下了深情厚意,留下了抹之不掉挥之不去的往事情缘。每每想起,宛如晨光中的草原牧歌,暮色下的云光霞佩,伴随着悠悠马头琴声,随风飘荡、款款而至。
对于内蒙古的认识,在我当兵远离家乡前,甚至说在五台山脚、皇城根下,都来自于中学课本,草原四季是模糊的,空间地域是抽象的,是一首北方民歌《敕勒川》,把我带入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男儿血,英雄色。为我一呼,江海回荡。山寂寂,水殇殇。”纵横奔突显锋芒”的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
记得,第一次去内蒙出差是隆冬季节,整个蒙古高原都笼罩白雪皑皑之中,工作之余,带着忐忑的心情,去寻找孩提时代熟知的诗里光景,除了蒙古包内悠悠的马头琴声、舌尖间的美味、酒桌上的奔放热烈,映入眼帘的景色与诗中描绘的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心里着实有些失落。后来,随着造访内蒙古的次数增多,特别是亲莅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在不断探寻隐藏蒙语称之为“心脏”的朱日和的 “成吉思汗边墙”遗迹过程中,穿过了春夏秋冬四季,走过了城市、草原、大漠戈壁,一次次地聆听穿越沙漠冰河草原的马蹄声,对蒙古高原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了深层次地感性认识。每到夜晚,从大漠孤烟深处、边防哨所回到住所,与战友们围坐在一起,吃着手把肉,喝着草原烈酒,唱着草原歌曲,聆听战友口述一代又一代戍边官兵一个又一个酸甜苦辣的故事,巍巍的兴安岭是他们的魂,挺拔的樟子松是他们的身影,边关小院永远是他们的牵挂,也给我余生留下了许多遐想。
军旅时光就像河流一样,缓缓流过。如今,我已回到桑植故里多年,不经意之中打开封存已久的像册,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念军营生活的日日夜夜,想念曾经战斗在大漠戈壁的日子,耳际萦绕的是优美歌声,眼前浮现的是迤逦风光。
驱车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看那蓝天白云下成群结队信步觅食的牛羊,星罗棋布的毡房升起袅袅炊烟,落日下最后一抺余晖,使天空变成色彩斑斓的挂毯,映照在大漠戈壁深处,绿绿的牧草从脚下延展到远远的天边,就好像整个宇宙都是绿色,在这望不到边的绿色中盛开着美丽的花朵,不远处草丛中惊飞的鸟儿,沟壑旁窜出的兔儿,让人陶醉,让人留恋。
运筹帷幄于朱日和演兵场,登上察汗敖包丘陵极目远眺,一望无际的草原映入眼帘,心头一下子就涌上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思古幽情,置身在“成吉思汗开始第一次西征问罪花剌子模、康熙大帝大阅兵后征剿噶尔丹、袁世凯击溃外蒙叛军”古战场,千里之外精确制导武器已枕戈待旦,空中战鹰伴随着轰鸣声从头顶呼啸而过,远处战车铁流滚滚战火纷飞,年轻的士兵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奋力冲向阵地,厮杀声响彻于九霄云外,让人震撼,让人沸腾。
心扉回荡的是酒的世界歌的海洋,感受到了蒙古族文化的奔放与热情,歌声和烈酒已诗化成她们民族的符号,歌是欢乐的使者,酒是友谊的桥梁,以歌兴酒,酒兴舞起,达到了生命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怀念喝过的香甜奶茶、吃过的纯手工的奶酪和牛肉干等美食,怀念蒙古民族热情豪迈的生活,不断撕拆尘封已久的草原情结,让人怀旧,让人牵念。
思绪萦绕在“千年枝繁叶茂,千年衍生不死,千年默然站立,千年虽死不倒,千年历尽荣枯,千年倒下不朽”的胡扬林,注视着她顶着戈壁滩上的烈日迎着大漠的狂风巨沙,吮吸着脚下土地中贫瘠的盐碱养料傲视苍穹,催生了妩媚的风姿、倔强的性格、多舛的命运,以春夏绿、深黄、冬红的多变,赋予了人类太多的诗情与哲思,用它的忠诚和勇敢不屈,死守大漠千年万载,诠释生命的价值和力量。古往今来,已成为一种精神而所被人们膜拜,让人神往,让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