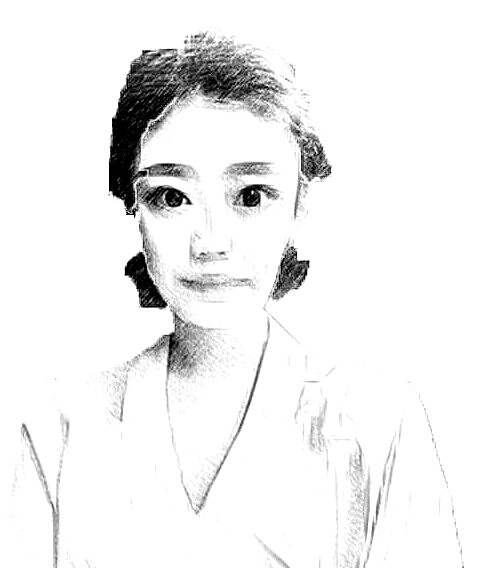这个展览到村长家了!当村落与先锋艺术装置相遇,当绵延千年的东方美学与当代国际策展语言共振,乡村不再只是乡愁的载体,而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学实验场。中国艺术展为何选择扎根乡土?传统美学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激活新的生命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陈慧娇回归乡村对话国际策展人金冈。这位曾操刀国际艺术的策展人,正尝试以“在地性”为锚点,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城市白盒子空间移植到麦田之间。在他看来,乡村的肌理不仅是展墙,更是文化基因的活态容器——“在这里,艺术家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的创作,能否与这片土地上流动千年的呼吸对话?”这场展览,或许正是一场关于传统复魅与文化出海的预演。
陈:您如何定义“艺术作品”?它与城市艺术作品有何不同?
金冈:艺术作品通常指艺术家通过创造性表达传递审美、思想或情感的创作,具有独立艺术价值,常见于美术馆、画廊等专业空间。城市艺术作品则是融入公共环境的艺术形式,如壁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强调与城市空间、公众的互动性,兼具功能性与文化传播目的。两者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个人表达,后者注重公共服务与空间活化;前者多在封闭场馆,后者嵌入开放城市环境;后者常结合实用功能,如公园座椅、照明等,前者艺术性更纯粹。
陈:我认为艺术作品到乡村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您认为这个展览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如何?您是如何选择艺术作品进行策展?有哪些标准?
金冈:您提到的观点很有价值。艺术作品进入乡村确实能产生独特的共鸣效果,这种“接地气”的展示方式往往能打破艺术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乡村的自然环境、生活节奏和民俗气息,更容易让观众在熟悉的场景中感受到艺术的温度。比如在开幕式之前有党建龙老师在墙壁上画了一幅描绘三个小孩在田野放风筝的作品,正是“春分”节气蔡家坡村麦田里出现的真实情景,能直接唤起观者对土地的情感记忆。
这类在地性艺术展览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具有积极意义:打破美术馆围墙,让艺术回归生活本源,拓展了艺术展示的边界;用艺术语言重新诠释乡土价值,增强文化自信,激活乡村文化;通过作品反映城乡差异、传统与现代碰撞等现实议题,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对话。
当然我们在策展时主要遵循三个原则:一、主题在地性:作品内容要与当地自然或生活产生关联,比如创作的节气书法和乡村人物的绘画作品就是表现乡村劳动生产的时间节令,还有终南山和花鸟题材绘画作品,都是突出主题的在地性。二、形式亲和力:避免过于抽象晦涩的表达,优先选择视觉冲击力强或互动性高的作品,以大家熟悉的节气及农忙习俗的习惯,在瓦片上书写,在墙壁上绘画。三、互动参与性:让乡村叙事更加丰富多彩,在开幕式之前艺术家在地创作,亲身体验艺术创作过程带来的视觉美感,同时也开设了公共教育课程,观者与艺术家同画一幅画,在同一个空间相遇。
陈:您如何看待乡村艺术与城市艺术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意义是什么?
金冈:乡村艺术和城市艺术的融合就像把两种不同的食材放进同一个锅里炖,既能保留各自的风味,又能碰撞出新的味道。具体来说,乡村艺术像地里长出来的作物,带着泥土气和生活气,比如用老瓦罐拼贴的壁画、用麦秆编织的装置。城市艺术则像工厂加工的创意产品,比如会发光的钢结构雕塑、能互动的数字投影。两者结合后,既能让城里人看到“会呼吸的艺术”,也能让村里人接触到“会说话的科技”。
这种融合带来的“营养”价值让艺术更“接地气”,城市艺术家到乡村采风,能从真实生活中找到新灵感,避免作品变成空中楼阁;让乡村更“有生气”,艺术装置入驻后,有些空心村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带动了民宿、手工艺等产业;让文化更“有底气”,传统技艺通过现代手法重新包装,比如皮影戏配上电子音乐,年轻人更愿意传承。这种融合就像给老房子重新设计给安上落地窗,既能看见窗外风景,又能让阳光照进来。
陈:在策展中,您如何平衡乡村艺术与城市艺术的表现形式?
金冈:在当代策展实践中,平衡乡村艺术与城市艺术的表现形式需从多维视角切入,既要尊重两种文化生态的独立性,又需构建对话桥梁。首先,主题策划应提炼共通的精神内核,如将“乡村记忆”与“都市生存”并置,通过传统书画、装置艺术、影像记录等媒介呈现不同空间维度下的人类情感叙事。其次,书画家的乡村叙事需打破传统展区分割模式,采用对话联动的展陈设计,乡村叙事对节气叙事,花鸟叙事对终南叙事,例如用编织装置连接乡村手工艺与城市数字艺术,形成视觉与触觉的通感体验。再者,技术赋能可创造跨界可能,乡村艺术家可借助AR技术重构民间故事,城市创作者则可采集田野录音进行声音艺术创作。教育板块需设计双向互动机制,邀请乡村艺人开展传统工艺工作坊,同时引入城市策展方法论培养在地文化自觉。最终,平衡的本质在于消解二元对立,在差异中寻找生态共生的可能性,使展览成为城乡文化基因重组的实验场域。这种平衡策略既保留了乡村艺术的在地性温度,又赋予城市艺术以人文深度,最终在差异中构建起文化共生的当代叙事。
陈:您如何设计展览空间以更好地呈现乡村艺术作品?
金冈:以“著手成春”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展空间设计,需构建“农民画”与“文人画”的双重叙事对话。首先采用“分层”空间结构,将展厅划分为上下两层,一层为馆藏经典农民画,二层为围绕乡村的书画艺术创作,以“乡村-节气-花鸟-终南”四重叙事方式,分别对应乡村艺术的材料源头、技艺传承、当代转化与创新实验。地面铺设当地红土与碎陶片混合的肌理,墙面以竹编网格为基底,悬挂不同地区的传统农耕工具,形成立体的文化根系图谱。
陈:在策展过程中,您如何确保乡村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不被误解或曲解?
金冈:“著手成春——书画家的乡村叙事”展览遵循策展方案的核心原则:让乡村艺术成为“自我言说的主体”。策展的本质是搭建“文化转译”的桥梁,而非替乡村艺术“代言”。通过赋予在地创作者阐释权、保留文化语境的复杂性、拒绝简化的符号消费,才能让观众理解:乡村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美学形式,更在于其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完整表达——就像陕西剪纸中的“鹿鹤同春”,只有知晓其背后“祈雨仪式”“耕读传家”的文化语境,才能真正读懂书画作品深处的耕读智慧与精神寄托。
陈:您认为乡村艺术作品对乡村社区有何影响,艺术作品是否能够帮助乡村地区实现文化振兴?
金冈:乡村艺术作品对乡村社区的影响具有多维度赋能作用,是文化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非功利性”与“对话性”。当乡村艺术以平等姿态参与文化交流(如农民画与文人画同空间展示),它不仅是被消费的“景观”,更是传递乡村价值的“信使”。乡村艺术的振兴价值,本质在于其作为“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对内凝聚认同、激活传统,对外建构叙事、连接世界。当艺术创作与乡村内生需求深度绑定(如保留技艺本真性、尊重村民阐释权),而非沦为政绩工程或商业噱头,它便能真正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沃野”,让传统在当代生活中自然生长,实现“以艺润村,以文化人”的可持续发展。
陈:您如何看待乡村艺术与生态艺术的关系?艺术融入乡村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艺术语言?
金冈:乡村艺术与生态艺术本质上是共生共融的文化实践,二者在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上高度契合。乡村艺术天然蕴含着与自然对话的基因——云南哈尼族用梯田肌理创作大地艺术,陕北农民以窑洞夯土塑造雕塑,这些实践本身就是对“天人合一”生态观的视觉化诠释。生态艺术强调的可持续材料(如秸秆、陶土、旧农具)与乡村艺术的在地性材料传统完全重合,二者共同构建了“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的创作逻辑。贵州黔东南的“稻田艺术节”,艺术家与村民合作将废弃渔网编织成稻田装置,既修复了水域生态,又让传统渔耕文化以当代艺术形式再生,证明乡村艺术是生态理念最本真的载体。
艺术融入乡村之所以可能成为全球化语言,在于其承载的普世议题——生态危机、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正是人类共同关切。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将雪国乡村转化为国际艺术现场,西班牙“大地艺术之都”Arcos de la Frontera用橄榄林装置探讨干旱地区生存智慧,这些案例证明:当乡村艺术提炼本土生态经验(如灌溉系统、节气农耕)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就能突破地域限制,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媒介。中国浙江松阳的“茶香诗路”艺术计划,通过茶田行为艺术、竹编灯具展,让西方观众理解东方“道法自然”的哲学,正是本土经验向全球语言转化的成功实践。
乡村艺术与生态艺术是同一命题的两面——前者是地域生态经验的文化结晶,后者是全球生态危机的艺术响应。当艺术融入乡村以“守护自然肌理、激活本土智慧”为核心,而非简单移植西方范式,就能形成兼具独特性与共通性的表达体系。这种基于“地方-全球”连接的艺术实践,既能为生态艺术提供最鲜活的田野样本,也让乡村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文化发声体,最终实现“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的艺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