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歇。七七事变后,在祖国大陆的台胞纷纷申请恢复国籍,成立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成立的台湾义勇队作为抗战时期由台胞组成,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一支队伍,是台胞参与祖国抗战的杰出代表。福建作为台胞聚居大省,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台胞安置与抗日力量集结的关键区域。崇安(今武夷山市)虽非抗战前线,却因独特的地理与社会条件,成为福建台胞安置的核心区域之一,更与台湾义勇队形成紧密关联。本文依据福建省档案馆编《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中与崇安相关的台民安置文电、兵员输送记录、家属救济函件等资料,梳理崇安与台湾义勇队的互动历程。
一、崇安是抗战时期福建台胞的集中安置基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防范日军利用台胞进行间谍活动,同时保护台胞安全,福建省政府决定对分散在福州、厦门、晋江等地的台胞进行集中安置。崇安因地处闽北腹地,山深林密,远离沿海战火,且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适宜垦荒生产,成为重要的台胞安置点。
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下达指令:“将晋江县政府解省之台民254人与省会遣留之台民151人一并解往崇安,由该县政府妥筹安置,并由保安处派队护送。”1939年8月,连城县因“成为交通孔道”,“将留县台民54名移往崇安”,至此崇安台胞规模达400余人。为便于管理,崇安县政府将台胞安置在孔庙与贞光学校,形成有组织的居住体系,分为壹保、贰保、叁保等区域,涵盖医业、垦荒、手工业、商业等不同职业群体。
为保障台胞生活,崇安县政府从基本生活、生产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初期按“成人每日0.10元,孩童0.06元”标准发放伙食费,解决台胞温饱;1939年3月,为应对寒冬,崇安县政府“制发棉被20件,转发旧棉衣173件”,由垦务所转交台胞;1941年5月,福建省振济会拨发2000元救济费,分配给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每人“补助金37元7角3分6厘,计53人”,以缓解生活压力。
生产就业支持方面: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崇安县垦务所先后批准邓秉仁、曾子炉、陈光复、王仲甫、黄国瑞等多户台胞“补编垦荒”,分配耕地与农具,鼓励台胞“自耕自食”。“抗战期中军用原料之樟脑与樟脑油国内极感缺乏,价格腾贵”。1939年2月,垦务所支持台民朱春海等利用崇安丰富的樟树资源创办樟脑工厂,“将来所得利益,即充留崇台民用费,以补垦荒之不足,而国家亦获得军用品原料,实一举两得”。
教育医疗服务方面:1940年1月,崇安垦务所筹备“台童教养所”,解决台胞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将叶逢春、张亨寅等17名台籍医生安置到县卫生院及各区卫生所,既解决台胞就医需求,也补充地方医疗资源。这些政策不仅稳定了台胞生活,更消除了台胞的“异乡感”,为其参与抗日工作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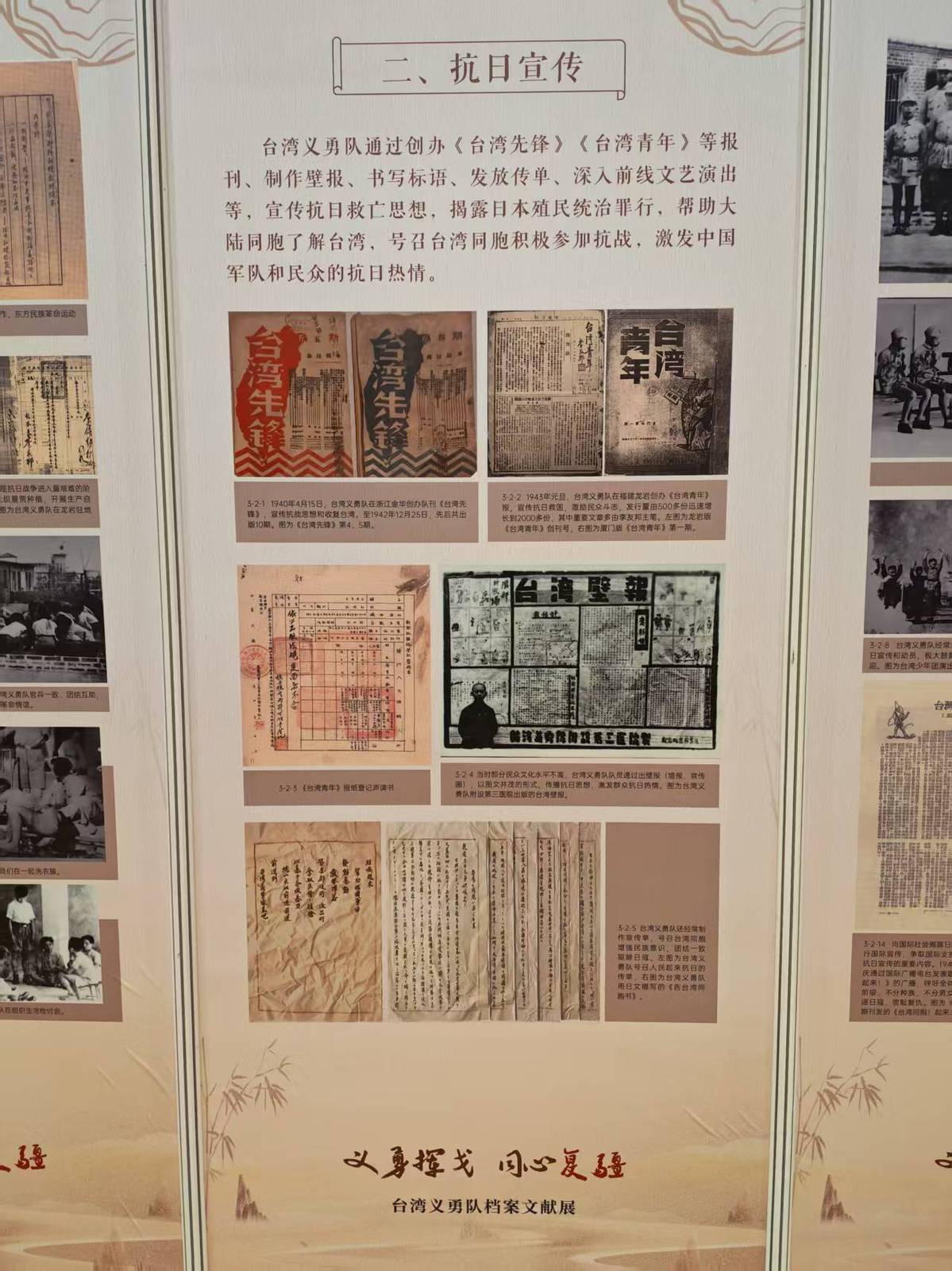
二、崇安是台湾义勇队的重要兵员来源地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台胞领袖李友邦和中共地下党员张一之的率领下,于浙江金华宣告成立。崇安集中的台胞中,大量青壮年具备爱国热情与专业技能,成为义勇队最重要的兵员来源地。
早在1938年11月,李友邦便从浙江辗转来到崇安,与张一之一起动员组织崇安的台胞参加抗战,受到了台胞的热烈响应。1939年1月,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由李友邦、张一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5人任筹备委员。为了动员组织台胞参加抗战,崇安县政府于当月设立“台胞战地服务训练班”,并制定详细的《训练班简章》《训练办法》与《服务优待办法》等。《训练班简章》明确规定:“训练班系以训练确愿效忠祖国,参加战地服务留崇台胞,使具有充分之军事、政治、医疗等学识及技能,确能前往参加战地服务,增加抗战力量为主旨。”《训练班简章》还规定训练班“分设军事政治及医疗两组”。《训练办法》规定:“本班军事训练占50%,政治训练占44%,精神训练占 6%”;“本班训练期内学员伙食、服装均由本府供给”。《服务优待办法》规定:“各学员开赴服务后,其家属除已在垦务所垦荒外,其生活困难者,由本府[津]贴成人每日1角,孩童7分”;“出征台民,其子女得免费入本县各学校读书”;“学员在各部队服务,如有伤亡,得呈请相当抚恤之”。
训练班的举办点燃了台胞的参军热情。从1939年2月至1944年9月,崇安向台湾义勇队输送兵员超百人,占义勇队队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1939年2月,李友邦从崇安挑选郭汝侯、黄国瑞等22名台胞(另有其子女6名儿童)作为第一批队员赴金华集训,离开崇安时留崇台胞和当地人民开大会热烈欢送。3月,在张一之率领下,石崑玉等第二批22名台胞赴浙集训,福建当局派兵站专车护送,并提供军装、路费等。此后,崇安台胞参军热潮持续高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陈春圃、曾慧英等台民主动申请赴浙;1940年6月至8月,李瑞成等14名台胞、朱炳源等20名台童及13名队员家属组成52人队伍,在牛光祖率领下赴浙。1941年3月,柯水治、高聪明、廖月英3人赴浙;1941年12月,张之杰、简荣铨、林金妹、石志英4人赴浙。这些台胞带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信念,在义勇队中承担医疗、宣传、情报、对敌喊话等任务,成为义勇队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崇安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休整与家属安置后方
抗战期间,前线战事紧张,医疗条件有限,需要后方提供稳定的休整场所与家属安置支持。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之下,崇安凭借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完善的台胞管理体系,成为台湾义勇队队员休整与家属安置的“后方港湾”。
1939年至1940年,多名义勇队队员因伤病返回崇安休养。1939年4月,队员李国星因病返回崇安,县政府为其提供诊疗;5月,队员翁鹏飞、李国明相继返回崇安,垦务所专门安排宿舍供其疗养。为规范管理,台湾义勇队与崇安县政府建立联动机制,队员请假返崇需由义勇队出具公函,明确请假期限;痊愈后由崇安县政府协助归队,确保队员休整与作战两不误。
台湾义勇队队员家属的安置是稳定队员军心的关键。对于队员家属,崇安县政府给予了细致关怀。1940年起,福建省政府批准义勇队队员家属赴浙团聚,邓秉仁之妻林美良、黄授杰眷属许淑娟等先后经崇安中转。1942年6月,因“时局紧张”,67名队员家属从崇安迁移至建阳,崇安县政府负责护送与物资调配,并造具《台湾义勇队眷属姓名册》。此外,崇安还为队员家属提供教育、医疗等便利。这些举措解除了队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抗日工作。
从《台湾义勇队档案(1937-1946)》可以看出,从台胞安置到兵员募集,从队员休整到家属关怀,崇安与台湾义勇队的互动贯穿了抗战始终。在崇安的支持下,台湾义勇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从初期63人增至1945年的381人,在宣传鼓动、战地医疗、对敌政治工作等方面屡立战功;而台湾义勇队的存在,也让崇安成为两岸同胞共同抗战的象征地,彰显了“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共同信念。这段历史不仅是台胞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今天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共护民族大义的重要历史依据,激励着两岸人民铭记共同抗争的岁月,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