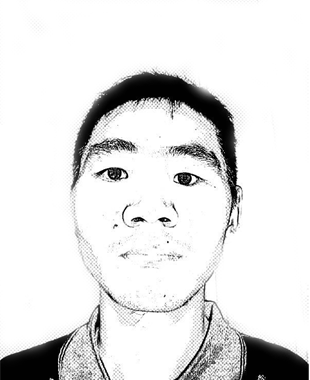金何
走在街上,前方一对亲昵的情侣引起我的好奇,待到再仔细看,竟然是两个男生。我不禁想起了高调宣布出柜的蒂姆库克以及李银河。
“心理疾病”、“流氓罪”,你可能不曾想到同性恋身上贴有这样的标签。虽然在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承认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是心理异常,但这个群体是否真的已经被大众接纳,还是有待商榷的。
它神秘、边缘、小众,尤其在艾滋病出现之后,这个群体就一直被前者纠缠不放。谈及他们,媒体更愿意用“同性恋问题”而非“同性恋现象”。说到它,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西方对待这个群体是如何如何开放,而处于东方的我们是异常保守的。
这样的想法恰恰错了。
《圣经·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如此写道:“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信奉上帝的欧洲人,对待同性恋,判刑从苦役到监禁到火刑或者活埋不等。即便是从后来的文艺复兴一直到20世纪,西方社会对待同性恋也一直是暧昧模糊的。
而一个可能会让现代人大跌眼镜的事实是,在古代中国,对待同性恋群体反倒开明许多。
清代学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2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不靠谱,毕竟连黄帝是否确有其人还难以考证。
但无论是汉文帝宠幸邓通,让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因“色”获益最多的男人。还是到宋朝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成风月作坊,以至于到了宋徽宗时,不得不立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这都说明,狎昵娈童的同性恋,从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渐渐扩散到社会民众中,并且被大众所接受。
而处于汉宋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好男风,这个时期十分讲究品性姿容,这倒跟中世纪之前的古希腊的崇尚同性恋不谋而合。
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关于同性恋的一切似乎都是围绕男人进行的。难道同性恋仅仅是男人之间的事吗?女人又去了哪里呢?
《西游记》里有一个女儿国,或许我们不曾想过,在一个没有男人光临的地方,她们的性又是如何解决的,或者说女儿国里全部的人都是同性恋?不过吴承恩老先生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女人喝水就能怀孕繁衍后代的情节,似乎算是解决了人口繁衍的问题,但关于“性”,似乎就这么遮遮掩掩的过去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另一部小说当中的虚构之地,《镜花缘》里,我们的男主角也到了一个全是女人的国度。但是跟前者比起来,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里有男人存在,但统治社会的是女人,男人和女人的身份,除了怀孕这个生理因素,其他方面都跟外面的主流社会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置换。
这两个虚构的乌托邦国度跟现实比对起来,又是一样的。若女儿国王不懂性,为何见了唐御弟便拴不住心猿意马了呢?而在《镜花缘》里,男女社会身份的置换,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女权主义直观的描写了——虽然这是一个虚构之地。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或许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能让你我明白一二。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或许并不仅仅满足于异性恋,时不常的可能还有搞基的嗜好。而处于被选择地位的女性,由于是处于一个支配的地位,她们不但失去了“性”的自由,更不会有恋的美好。
有性,就会有生理压抑,压制不住了,就需要发泄出来。汉武帝时,由于皇后陈氏无子,恩宠日衰,孤独苦闷之中,便命宫女穿着男子衣冠,与她同寝一室,相爱如夫妇。不想此事被武帝发现,废除了她的皇后封号,贬至长门宫居住。看来无论是虚构的女儿国,还是现实世界的封建社会,女同性恋的出现都是顺理成章的。
只是相较于男同性恋的公然形诸歌咏,女同性恋之间的私密性更浓厚一些。这种私密性是迫于男性的支配地位,女子同性恋存在容忍甚至赞赏的观念,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习俗,只要不触犯“男女之大防”,女子之间相恋无伤大雅。因此无论是独锁深宫的女性,还是士大夫家中的大家闺秀,抑或是小家碧玉,主仆之间,发生点什么关系,生理和心理上,都是迫切需要的,这应该就是现代科学所谓的“境遇性同性恋”吧。
“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趋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朝市丛载》里的这首诗,说的是清代男同性恋坐马车过街的场景。由于清代禁止官吏嫖妓,客观上堵住了一部分达官贵人通过异性发泄的渠道,因此,男同在这一时期颇为流行。同样,人们对女同的态度也更加宽容,这一时期男同性恋互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则结拜金兰。
人们或许会有疑问,为何三纲五常如此森严的国度,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却是如此宽容,看起来不符合常理,但实际上颇符合常理。古代社会,家族延续和人们的感情生活是分开的,更不要说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庸,男人可以随时随地纳妾。在没有一夫一妻的法律约束下,只要保证了香火的延续,其余的事情就可以随便了。再加上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客观上给男男、女女的相处增加了便利和机会。
所以,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男性同性恋是潇洒的玩,女性同性恋除了性的宣泄之外,还有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某些同性恋,仅仅就是精神恋。因此看来,在森严的封建时代,只要不挑战男人的权威,社会就默认了女同的存在,虽然她们没有男同性恋那样好的境遇,不能公开渲染。
时代变了,套在同性恋身上的枷锁不但松动了,而且由于女性地位的提升,使得同性恋已经不再有男女之间的双重标准。同志一词有了另一层含义,基友等词汇在公共舆论里自由穿行,但大众对同性恋的了解,还是遥远且模糊的,人们对他们的心理,生活等等一切都是陌生和不成概念的。
这是因为在近代,一方面是精神病学的兴起,导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外都把同性恋定义为精神有问题。试想面对一个精神病人,人们难道不会感到不安和害怕吗?另一方面,一夫一妻制法律化之后,家族延续和夫妻感情生活合二为一了,这跟西方基督教一夫一妻的传统是一样的,自然,同性恋的社会生存土壤就消失了。这也正是为何很多人要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缘故。最后,我们曾经有一段道德洁癖时期,那个时候别说同性恋,就是异性恋在公开场合做出亲昵举动,都会被当成作风问题,并因此得付出代价。
这一切导致我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化。虽然舆论空间宽容了,曾经的缄默,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调侃,道德围垣看似松动了,但实则并没变。公共环境转变了方式,改变过去的单纯排斥,给了同性恋一片自由的天地,这片空间与主流社会是绝缘的,任其自身自灭。
作为一个可以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媒体和受众忽视的群体,对同性恋的宽容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媒体所能做的走出困境最基本办法是 :给予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更多的理解,而不是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报道的时候尽量不歪曲,或者不会为了争夺眼球而故意使用一些夸张失实的词语,少使用有色标签。公众不应该纵容媒体的歪曲,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看客,而应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这大概是有效而唯一的出路。